杜甫:伟大也要有人懂
编者按
杜甫忧国忧民、悲天悯人的精神受到万世敬仰。他毕生的饥寒流离,往往被看成造就“诗圣”的前提条件。但“诗圣”的称号只是后人对他的人格和“圣于诗”的艺术成就的一个综合性评价,杜甫从来没有把自己看成超越世人的圣贤,恰恰相反,他在诗歌中塑造的自我形象,始终是一个执着孤独、不合时宜的“腐儒”和穷愁潦倒、寂寞困苦的“少陵野老”。
前段时间由BBC出品的纪录片《杜甫》在各平台被热议,人们感慨为何与杜甫同处一个国度的我们没能拍出这样好的纪录片,就像我们曾经感慨为何与杜甫同处一个时代的人们没能发现杜甫的伟大。与其身后诗名相比,杜甫生前体会更多的是一种“乾坤一腐儒”的孤独感。

纪录片地址:

翻译成朝鲜语的杜诗
本文节选自葛晓音《杜诗艺术与辨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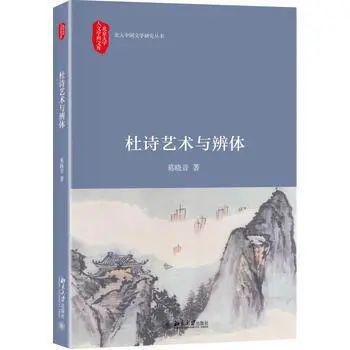
中国文学史上的大作家都有程度不同的孤独感,尤其是先秦汉魏六朝至初盛唐的诗人。失意困顿的遭际、缺乏同道的寂寞、对理想和操守的坚持、对世俗的洞彻和鄙视,是他们产生孤独感的共同原因。
而就不同时代、不同境遇的诗人而言,其孤独感又有不同的内涵。提炼孤独感的艺术方式的差异,往往会造成诗人不同的艺术个性。如屈原以香草自饰、独清独醒的孤洁,阮籍独坐空堂、徘徊旷野的茫然,陶渊明面对“八表同昏”、独酌思友的寂寞,李白天马行空、从云端俯视人寰的清高,都与他们构筑的独特的艺术境界有关。
不过,虽然比兴和构思的方式不同,其艺术提炼的原理却是相同的,这就是以诗人高大伟岸的个人形象与污浊荒漠的世俗世界构成反差强烈的对比。这也可以说是盛唐以前诗歌浪漫精神的表现传统之一。

杜甫同样体尝了屈原、阮籍、陶渊明和李白诸家大诗人的各种孤独感,而且愈到晚年,他对孤独心境的提炼也愈益自觉。去世前一年他称自己为“乾坤一腐儒”,就是对自己与整个世界的关系经过反复思考之后的最后概括。
与其他大诗人相比,杜甫最大的不同是:在个人形象和广漠时空的对比中,诗人突显的是自己的渺小和无力,然而其思考的深度和高度却迥出于前人之上。
01
人生大志与政治挫败感
杜甫一生曲折的经历,并非总是和孤独感相伴随的。大致说来,当杜甫处境顺利、不愁生计时,他对生活的浓厚兴趣是诗歌灵感的主要来源;当他身陷贼营、卷入战乱时,他对国运和民生的忧虑也使他无暇顾及个人的失意。而在困顿穷愁之际、羁旅漂泊途中,对于人生归宿的思考和寻求,才使他产生了强烈的孤独感。
早年的杜甫与李白一样,以大才自许,具有高远的志向。当他十四五岁时,便能“出游翰墨场”,被“斯文崔魏徒”比作班固、杨雄:
“脱略小时辈,结交皆老苍。
饮酣视八极,俗物皆茫茫”。
初次科举落第,也没有影响他对前程万里的信心。远望泰山时,他曾豪迈地宣称: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看到气势凌厉的画鹰和胡马时,便想象自己将来也会像鹰和马一样,
“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
“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
正是这种不甘凡庸的追求,使他日后对人生的挫败感更加敏锐。
十年困守长安期间,杜甫感受最深的是无人援引的悲哀。“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遭际使他初次产生了没有归宿的孤独感:
“长安苦寒谁独悲,杜陵野老骨欲折。”
“圣朝亦知贱士丑,一物但荷皇天慈。
此身饮罢无归处,独立苍茫自咏诗。”
天宝十载献赋长安,玄宗命宰相试文章,曾一度激起他的自信和希望:
“忆献三赋蓬莱宫,自怪一日声辉赫。
集贤学士如堵墙,观我落笔中书堂。”
然而以“文彩动人主”的辉煌转瞬即逝,
“破胆遭前政,阴谋独秉钧。
微生沾忌刻,万事益酸辛。”
妒才嫉贤的李林甫摧毁了他“奋飞超等级”的幻想,使他重新落入“愁饿死”的境地。
“酒尽沙头双玉瓶,众宾皆醉我独醒”,
经过这一番挫折,此时的杜甫已经尝到屈原式的独醒滋味。但是他从小立下的人生大志并没有动摇,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他一方面抒发着仕既不成、隐又不遂的悲哀,一方面执着地坚持自己甘愿被“同学翁”取笑而绝不放弃“窃比稷与契”的志向。这种志向已经不是出于个人的“稻粱谋”,更重要的是发自“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浩叹。
安史之乱爆发以后,穷愁失意的诗人又增添了一层死生无常的忧虑:
“垂老恶闻战鼓悲,急觞为缓忧心捣。
少年努力纵谈笑,看我形容已枯槁。
……
诸生颇尽新知乐,万事终伤不自保。
……
忽忆雨时秋井塌,古人白骨生青苔,
如何不饮令心哀。”
尽管诗人此时尚未垂老,但是形貌已经枯槁,唯恐埋没沟渠的忧思显然不是同饮谈笑的新知们所能理解的。因此,他无论是在与家人欢聚时还是在道路奔波中,都时时怀着穷独的恐惧:
“沉思欢会处,恐作穷独叟。”
“浮生有荡汩,吾道正羁束。
人寰难容身,石壁滑侧足。”
在“羯胡腥四海,回首一茫茫”的人寰中,他似乎预感到了此生因道不行而难以容身的艰辛。
从华州到秦州时期,是杜甫选择人生道路的转折时期。本来因逃难到行在,被肃宗授为左拾遗,在政治上有了施展的机会,此后直到两京收复,有了一年多参与朝政的历练。然而凭着一腔热血履行谏臣职责,却因疏救房琯而不小心触到了统治者内斗的痛处。从下狱到被疏救,最后被贬官疏远,政治上的挫败以及被众谤所伤的境遇给他带来的幽独感,较之早年的穷独失意是更深刻的:
“巢边野雀群欺燕,花底山蜂远趁人。
更欲题诗满青竹,晚来幽独恐伤神。”
他把中伤自己的小人比作野雀和山蜂,在经历了政治的风险之后,诗人已经体会到坚持清节的孤独。于是,非无沧海志的诗人开始了进退之间的选择。作于华州期间的《独立》诗说:
“空外一鸷鸟,河间双白鸥。
飘飖搏击便,容易往来游。
草露亦多湿,蛛丝仍未收。
天机近人事,独立万端忧。”
仇兆鳌引赵汸注说此诗“鸷鸟,比小人之媢嫉者,白鸥比君子幽放者”,这一解说虽不为无据,但杜甫在诗文中多处赞扬“鸷鸟”“以雄才为己任”“搏击而不可当”的“英雄之姿”,笔者以为这首诗里是以鸷鸟摩天搏击的姿态比喻“大臣正色立朝之义”,以河间白鸥往来容易的姿态比喻自由生活,两相并列,暗示了仕与隐的两种选择。草露和蛛丝也是以天机喻人事,就像政治生涯中常遭罪名罗织,令诗人忧思万端。思考的结果,他还是选择了辞官:
“平生独往愿,惆怅年半百。
罢官亦由人,何事拘形役?”
这种独往独来是指在精神上独游于天地之间,不受任何外物阻碍的极高境界。西晋到盛唐又为神仙家和佛家所使用,“独往”渐成为表示高蹈出世之意的常用词。对于毕生未能忘其济世之志的诗人来说,选择隐逸出世是痛苦的。这意味着他要对前半生执着追求的人生道路重新反省:
“万方声一概,吾道竟何之?”
陶渊明虽然也有过贫富交战的挣扎,但是他几乎没有问道的犹疑。而杜甫在选择了罢官之后,却因不知“吾道”之去向而茫然。这道,固然是实际的生存之道,更是自己的精神归宿之所在:
“百川日东流,客去亦不息。
我生苦漂荡,何时有终极。”
“大哉宇宙内,吾道长悠悠。”
从秦州开始羁旅漂泊的漫长道途,似乎是他一生寻求无着的象征。
杜甫在漂泊西南的十多年里,只有草堂时期的诗歌最为平和,抒发穷独之感的诗篇较少,其余的日子几乎都在贫病流离的境况中度过,所以孤独感与日俱增。首先是衰病困穷、故乡难归的孤愁:
“贫病转零落,故乡不可思。
常恐死道路,永为高人嗤” ,
“老魂招不得,归路恐长迷”,
“墙宇资屡修,衰年怯幽独”。
流落终生,到死后魂魄都不得归去的恐惧使他越到衰年,越是孤独。

杜甫草堂
其次是亲友音信断绝、天涯独处的忧念:
“海内风尘诸弟隔,天涯涕泪一身遥。”
几个弟弟都被烽烟阻隔,而在乱离之中,朋友也渐渐凋零,自己的存亡竟无人可托付:
“乱离朋友尽,合沓岁月徂。
吾衰将焉托?存殁再呜呼。
萧条病益甚,独在天一隅。”
再次是穷途漂泊、无处投奔的悲凉:
“真成穷辙鲋,或似丧家狗。”
严武和高适去世以后,杜甫在成都失去了依靠。在夔州虽然有柏茂琳照应两年,但也不是长久之计。离开夔州后出峡,一路寻访干谒,但屡遭白眼,无处可以久留。
“更欲投何处,飘然去此都。
形骸原土木,舟楫复江湖。
社稷缠妖气,干戈送老儒。
百年同弃物,万国尽穷途。”
在风尘漂泊之中看尽世态,尤其是各处官衙小吏的轻蔑,更加深了诗人的挫败感:
“羁旅知交态,淹留见俗情。
衰颜聊自哂,小吏最相轻。
……
狐狸何足道,豺狼正纵横。”
寄人篱下而饱尝炎凉的困境,使杜甫体会到阮籍在“走兽交横驰”的世界中的孤独。
“舟楫渺然自此去,江湖远适无前期”
这两句诗,为他前途渺茫、看不到归宿的漂流生涯作了形象的写照。
02
“吾道何之”的探索和疑问
除了生计无着的困境以外,杜甫最深刻的悲哀还来自于他对“吾道何之”的疑问。达与不达,只是个人的出处问题,而“吾道”是否可行,则是精神有无归宿的问题。“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是身为儒者的终极理想。因此即使在艰难流离之中,他仍然多次抒发过“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的慷慨意气;即使弃官,他还是时时流露出 “心虽在朝谒,力与愿矛盾”的遗憾。他在从秦州到达同谷时,住在凤凰台下的凤凰村。七岁就开口咏凤凰的诗人由此联想到西伯姬昌时凤鸣岐山的故事,产生了凤凰台上或许有凤雏在挨饿的奇想:
“我能剖心血,饮啄慰孤愁。
血以当醴泉,岂徒比清流?
所重王者瑞,敢辞微命休?”
凤凰向来被儒家奉为国家祥瑞。为重现太平之治,他甘愿剖心沥血,以生命来供养那可能被遗落的凤雏。这就是他身在江湖依然信守的“吾道”,但在现实中是否行得通呢?

在开元清平年代,历代士人理想中的凤凰确实一度出现。那时天下太平,经济繁荣,国力强盛,政治清明。正如杜甫在《有事于南郊赋》中所说:
“盖九五之后,人人自以遭唐虞;
四十年来,家家自以为稷。”
多少代人幻想的尧舜之世仿佛变成了现实。以张说、张九龄为代表的文儒型官僚提倡的礼乐政治,既迎合了封建盛世粉饰太平的需要,也展现了实践儒家政治理想的希望。他们从复兴儒学的角度提倡礼乐,得到玄宗的大力支持,并成为时代的共识。由于制礼作乐需要雅颂之文的配合,“文儒”的概念逐渐形成,它的含义就是“儒学博通及文词秀逸者” 。朝廷在开元十三年设立集贤殿书院,“延礼文儒,发挥典籍” ,专门征集鸿儒和文士。玄宗给予集贤殿学士无上的荣耀,充分肯定了文儒的政治地位和学术方向。文儒型官僚很快成为政坛和文坛的中坚力量,并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的命运。开元时代的著名诗人绝大部分受到以二张为代表的文儒集团引荐,天宝年间的文人受开元学风的熏陶,或受开元文儒所荐举,在所受教育、学问修养、政治思想等方面都具有鲜明的文儒色彩。
但是随着张九龄的去世,吏能型官僚李林甫的登台,开元时文儒在政治上的鼎盛时期到天宝时便一去不返了。杜甫后半生的经历证明在开元时期短暂的清平政治消逝之后,无论是在治世还是乱世,儒术都没有立足之地。天宝中他和元结等文士赴京师选举,被李林甫全部黜落,就是因为李林甫绝不会录用借制礼作乐献艺的文士。天宝十载,杜甫献三大礼赋,本来已经被玄宗命令待诏集贤院,但再次被李林甫黜落。这更说明李林甫作为一个天性忌刻的吏能型宰相,绝不会允许一个文儒通过进献礼赋而直至青云。杜甫当时就感叹“儒术诚难起”,后来李林甫下台,他又说“破胆遭前政”,说明他对前执政者李林甫排斥儒术文章是很清楚的。杜甫的悲剧典型地反映了这一代生长于开元时期,接受诗礼教育的文人被培养成文儒以后,在天宝排斥文儒的吏能政治下必然陷于困顿的共同命运。

杜甫画像,见于《晩笑堂竹荘画传》
战乱爆发后,肃宗排斥玄宗时代以房琯为代表的文儒,重用武将和勋官,儒术更无用处。所以杜甫深深感慨:
“兵戈犹在眼,儒术岂谋身。”
他虽然自比稷契,期望大用,但在实际的官场事务中又无可为用:虽然一度在肃宗朝做过拾遗,却因为疏救房琯而成为朝廷政治钩心斗角的牺牲品;在华州做地方官,又耐不住簿书的烦劳;在幕府参谋,更是“深觉负平生”;到白头为郎时,已是有心无力。杜甫致君尧舜的大志是开元一代文儒的共同志向,而杜甫仕途的坎坷也典型地反映了文儒理想与现实政治之间固有的矛盾。但是诗人一直以文儒士自居,战乱初起时,他说:
“伤哉文儒士,愤激驰林丘。
中原正格斗,后会何缘由。
百年赋命定,岂料沉与浮。”
感伤文儒士赶上这样的战乱,已经难料此生的沉浮。到临终前两年,他仍然说:
“推毂几年唯镇静,曳裾终日盛文儒。”
深深怀念那个文儒鼎盛的时代。杜甫在文儒政治的氛围中长大,与他关系较深的房琯、严武之父严挺之都是文儒的代表人物。因此他晚年对于盛唐的怀念,始终定格在一度实现了文儒理想的开元时代。但是即使战乱结束,太平再现,文儒之道是否就能用世呢?天宝时代还算是太平之世,却没有文儒生存的空间。以至杜甫在早年就曾愤愤地喊出过“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这两句诗看似醉言,其实是毕生埋藏在他心底的疑问:
“先生有道出羲皇,先生有才过屈宋。
德尊一代常坎坷,名垂万古知何用?”
羲皇之道加屈宋之才,正是文儒的最高典型。然而德尊一代者虽能名垂万古,生前却往往坎坷失意。更何况生当乱世,直到临死还看不见太平的希望,那么身为文儒士的现实意义究竟在哪里呢?难怪汉高祖说,为天下者不用腐儒。当杜甫晚年总结生平,自嘲为“腐儒”时,应当是彻悟了“文儒士”的这一悲剧和根本矛盾的。
杜甫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也是文儒的悲剧。“吾道”之不行使他只能屡屡作穷途之哭,发歧路之悲:
“茫然阮籍途,更洒杨朱泣。”
“苍茫步兵哭,展转仲宣哀。
……
不必伊周地,皆登屈宋才。”
君主昏庸,官资滥进,枢要皆为武夫,伊周之位已再也用不着屈宋之才。以文儒而致君尧舜的理想被现实彻底粉碎。
“天下尚未宁,健儿胜腐儒。
飘飖风尘际,何地置老夫?
于时见疣赘,骨髓幸未枯。
饮啄愧残生,食薇不愿余。”
天下虽大,却不但令他无处容身,甚至令他感到生为附赘悬疣。但是“腐儒”二字虽然概括了杜甫一生的悲辛,他却仍然以腐儒的道而自傲:
“甲卒身虽贵,书生道固殊。”
依靠武功谋富贵的将士,哪里懂得书生自有不同的“道”呢?
“安得覆八溟,为君洗乾坤?
稷契易为力,犬戎安足吞。
儒生老无成,臣子忧四藩。”
尽管腐儒至老无成,但是他依然相信洗净乾坤、安定天下的根本还是要依靠儒家理想的稷契大才。
“呜呼已十年,儒服敝于地。
征夫不遑息,学者沦素志。
……
周室宜中兴,孔门未应弃。”
中兴不能抛弃孔门之道,这是他的精神支柱。正是这道,给了杜甫终生不懈地批判时弊的勇气和关切国运民瘼的热情。正是对“吾道”的坚信,使他能将一介腐儒置于广大的乾坤中自我观照。腐儒虽然渺小,但是他所恪守的道是至大无边的可以拯救乾坤的真理。正如他自己所说:
“乾坤虽宽大,所适装囊空。”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乾坤又可以成为腐儒的囊中之物。这就是“乾坤一腐儒”这一理念概括的深厚内涵。正因如此,后人才会从这一对比中看到诗人的经纬天地之志,以及包容乾坤、与元气同在的精神力量。








发表评论 评论 (3 个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