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丨程继龙,陕西陇县人,生于1984年3月。文学博士,现供职于岭南师范学院人文学院、南方诗歌研究中心,致力于中国现当代诗学研究、诗歌评论。在《外国文学研究》《兰州大学学报》《艺术评论》《文艺报》《星星》等刊物上发表文章多篇,也写诗、散文。
新诗百年的艰难求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以前所未有的深度与广度书写现代人在现代社会里的经验,从现代汉语中提取资源又反向提升现代汉语的品质,拓展了人们表达世界和自我的方式,并且最终为生活于汉语圈的人们提供了一方暂可皈依的净土。 新世纪以来,行外人对诗歌的随意慨叹与哗众取宠自然不值得认真对待,但行内人的悲观结论却令人错愕,后一种行为实是出于情怀的衰减和立场的错位。今天提出这一话题,是在敬畏当代诗歌的前提下,就平时对诗歌、诗学积累的一些印象、看法,提出几点针对性的思考,随笔式地呈示出来,尝试对新诗的发展做出一点反省,引出一些对话。迷恋运动的力量
讲当代诗歌史,从一个个运动讲起,一波接一波,滚滚不尽,这成了一种常规思维,一种传统,离了“运动”,仿佛对诗歌无可言说,正如当代诗歌自身发展的实际情形那样,观念是运动的灵魂,而运动是观念的实体,诗歌借运动这个“势”以行。近代以后,几乎所有盛大的文化时代,都有一个运动作为先导。然而同时应当辩证地看到,任何有生命力的文化时代,都有一个漫长的,几乎不为人所知的生长阶段。社会学意义上的“运动”,当指大规模的有组织的群体性活动。当代人对运动的情结根深蒂固,这可能建立在一种特殊的历史观上,即历史分期的获得,主要靠一些具有界标性质的重大事件,例如,“武昌起义打响了反封建的第一枪”、“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由此划定出一个分水岭,分水岭的前面是旧的时代,后面是一个全新的时代,在“绵延的时间”(柏格森语)上分离出一个凸起的点,由此世界获得了新生,事物取得了意义,人们的世界观的建立变得有章可循。在这种新旧对立中,过往经验的存在是为了反证现在的正确,人们在一个断裂了的房间里打量散发着油漆味的新家具。
当代,似乎人们越来越不相信“个人”的力量,个人的能量只有放在无数个人与个人构成的网络中,才能走向历史的前台。的确,第三代诗歌和其他诗群一样,是真诚的,值得由衷敬佩的,然而那种阿Q“革命了”般的神情,实在可悲,实在引人深思。不久前的“下半身”“垃圾派”“低诗潮”,仍然遵从了这一古老的法则,当“下半身”宣告以下半身对抗一切上半身、形而上的时候,“垃圾派”高调宣布只有写垃圾是对的,而“低诗潮”以挑衅的语气宣称“引体向下”(张嘉谚《中国低诗潮》),宣称下半身只有掉在地上才是有意义的。当然,作为崇尚先锋的极端实验,补缺般地倡导穷尽之前视而不见的一种可能性不是无意义的,但是这种猴子搬包谷式的推进方式,负面效应也是显而易见的。搁置或者抹杀了前辈诗人们开凿出来的、有价值的值得进一步建设的命题,这是一个重大的缺憾。后辈诗人怀着怨艾的冲动造出来的代表文本,如果在一个稍长的时空范围里来衡量,未必具备经典的品质,甚至有时连是不是诗都要犹疑一下。这么说丝毫没有否定先锋实验的必要性的意思,当代诗歌的吊诡下任何结论都显得困难,只不过是想提醒,别太忘了诗歌“常”的力量,这是一种更为久远的状态,事物的发育尽管离不开瞬间的裂变,然而不应忘记恒河沙数般的默默渐变的瞬间。
很多东西是在积累与修正中慢慢臻于成熟的,当代诗歌在进程的模式上太缺乏慢声细气的雍容了,被燥热的力比多催迫,匆匆换场的诗人们应当留意一下大浪下面的静水,以便将手中的活儿做得细腻一些。“革命”之后是“改革”,在运动的第二天,诗人必须有抽身而退,进入个在生活的勇气。

“圈子”成为当代人存在的中介,成功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进入“圈子”,这在如今已成常态。“圈子”使我们想起“沙龙”,例如诗哲马拉美罗马街5号的“星期二沙龙”,孵化出瓦雷里、纪德、莫奈、德彪西等巨匠,深刻地影响了现代主义的进程。“新月派”的形成,离不开北平胡同林徽因家中“太太的客厅”、朱光潜慈慧殿三号的“读书会”,出入这里的英美留学生和隐士文人都对新诗有着特殊的思考,成为现代文坛的佳话。按理说,沙龙、圈子、群体之类是文学、文化生成与传播的正常途径,然而过度的狭隘的圈子化的存在方式,是有极大的负面效应的。诗歌正常的生存与发展应该是持有自己的立场,同时与他者形成对话。实际上放在一个大的尺度上来看,自我的见解和实验,常常是古已有之或众所周知的。真正的创新是艰难的。圈内的相互认同极易造成唯我独尊的幻觉,只见自己的倒影,不见整个世界。打破壁垒,使圈子开放化,是井蛙观海之举。当代社会悖谬式的格局,是本不精于生存的诗人,无奈抱团取暖,领悟了“进入现场”“活在当下”的迫切性,然而忘却了“争千古”的使命,在一个个小圈子之外,还有一个汇古通今的“千古”一直存在着,杨万里晚年吟道“只有三更月 知予万古心”,不纯是道学家的腐语。当代诗人纵使脱离不了一时一地的利害,也必须有这样一种抱负,如果他不是仅仅将诗作为一时的工具的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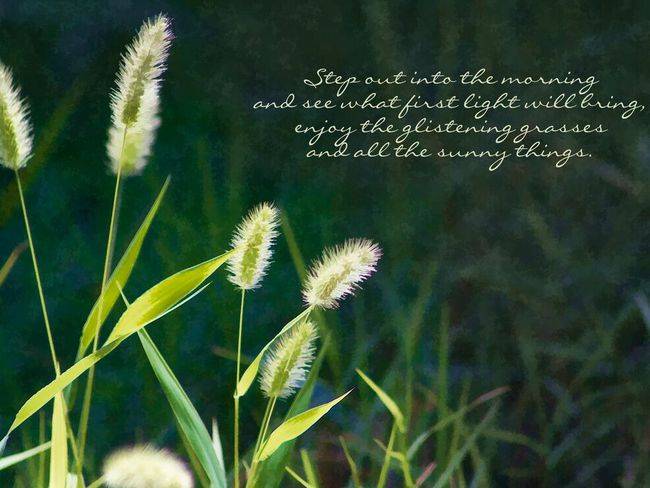
拘泥地看,当代诗歌的“经验”,是当代诗歌所着力表达的对象。当代诗歌对经验的书写,给人两种极端化的印象。一是肤浅的现实主义、写实主义,另一类则是毫不反思地沉溺于一己的私事、思想。这是两个极端。是时候重新认识“经验”与“个人”的关系了,单向度地迷恋“个人”是一个流行的错觉,无论是从社会学还是艺术学的角度来看,绝对的个人都是不存在的,一个人越是对自我、诗歌、人类文明理解得充分,就越能意识到艺术和文明的性质,越能在这一坐标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在诗歌中,毋宁说,“个人”之于诗,仅仅是一个起点,一个通道,然而却是一个不可或缺、最终要通向一个愿景的情思场域。在这里各种经验获得了共通性,是可以通约的,不再是难以理解的坚硬顽石。套用一句古话,诗歌是一种公器,交流和共享是他本身具足的一个功能。艾略特说他读《神曲》,最敬佩的是但丁写出了如此普遍而深刻的人类情感类型。第二点必须认识到,并非一切经验现成地就是诗。对当代诗歌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现在正处在一个“礼失求诸野”的阶段,纷繁的现代经验必须进入诗的场域,同时不断扩容,诗歌 “必须有/一个胃,能够消化/橡皮、煤、铀、月亮”(路易斯·辛普森诗句),所有当代诗人都处在这样一个经验与表达的共时性张力结构中。
但是,越是如此,越要能意识到“诗艺”的重要价值,注意是“消化”而不是“吞下”,诗艺是一种特殊的机制,它起化合的作用,将感觉、情绪、思想这些经验要素化合为诗,最终成为诗,能在“诗”的意义上成立。这个“化合”,不等于单向的提炼与升华,那是古典时代的做法,它还意味着向下、向侧面,向人类经验前所未到之隅旁逸斜出。诗歌到当代,已经海纳百川,当代诗人应自主取用一切资源,自由而充实地抒写时代的、历史的、现实的、个人的、内心的一切经验,同时是在“诗”的意义上处理这些经验,使它们成为诗的经验,进而进入文化,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另一种“史”。

当代诗歌似乎给人一种强烈印象,从主体角度来看,似乎诗人的主体精神状态越怪诞,就越被认为合格、理想。“愤怒出诗人”、“要写诗,先发疯”,疯狂、怪癖、自杀成为一名诗人特别的标志。“诗人之死”成为一个持续性的现象,这些诗人一方面视诗歌为生命的持存方式,另一方面以极端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诗歌与死亡之间的黑暗地带里的偶然或必然,成为热心者乐于猜测、谈论的话题。然而,不能简单将罪责归于大众的盲目,媒体的跟风和诗评家的草率。诗与人有着深刻的辩证关系,新诗本体与新诗主体是相互促进、相互塑成的关系。正在生成中的新诗同时也规约着诗人自身精神状态的走向,新诗对新型的审美主体的依赖程度远非古典时代可以想象。当代先锋诗歌求异、创新,竭力表达当代人在当代社会里纷繁复杂的感受,反过来又导引、塑造出非常态的诗性主体,正如王尔德所说“生活模仿艺术”。
实际上,诗人主体状态的孤绝、封闭在一定程度上是根源于现代主义诗歌的影响。新诗与西方现代主义诗歌有着至深的关联,西方现代主义诗人在自己的背景和传统中,借助诗歌所表达出来的悲观、绝望、尖锐、痛楚等“玻璃渣般的感觉”引起后发的中国诗人的强烈认同。但是,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问题也日益凸显。现在看来,虽然说不极端无以文学是对的,然而它仅仅是对的一途。很显然,怪诞、孤绝、残忍、神经质之类不等于诗,这么说也不意味着将诗歌等同于善良、和谐、“东方的韵雅”(闻一多语),诗歌的触须可以抵达任何文化领域。
应该看到,诗人的主体到今天应该多样化,诗人个人的主体状态也应该多样化,他可以是一个平凡的人,一个多情的人,一个孤愤的人,一个神圣的人,一个滑稽的人等等,这种多样,可以给诗带来更丰富多样的内涵与面向。应该走出单纯以主体的极端化来驱动诗歌的片面做法,在一个更宽泛、更灵活的态度下来建构诗性主体,理解诗与人的关系。在诗歌本体与诗歌主体的互动关系中,矫正现代主义的负面影响,着意培育出艺术感知力更为敏锐深刻、人格修养更为强健完善,可与当代现实、文化同步对话的新型主体。

读者、批评家、研究者如何介入评说诗歌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言说诗歌的话语,是一整套用以界说、解释、评价诗歌的语词、陈述。这一话语体系与诗歌平行发展,建立在多学科知识成果和当代诗歌实践的基础之上。严格来说,当代诗歌尚没有建立起一套较为大家所认可的言说系统。当代诗歌批评、研究面对“诗”这个老搭档,常常处于失语状态,难以真正进入诗歌纹理内部,缺乏将艺术特征和精神特质呈现出来的能力,不能实现诗人与解读者之间的精神对话,更不能提炼出具有普遍性的诗学命题。即使是一小部分诗学家苦心经营出来的诗学体系,冷静审视,其存在之基仍不够坚固。
当代诗歌言说话语中能经得起考验的成分仍然不多,能称为知识的部分仍然十分有限。在多疑的时代,这一问题尤难解决,一方面需要个在的诗歌知识人经过深入考察与思考之后的个人尝试与建设,另一方面需要所有诗歌知识人的协同合作。诗学就像语言的生成发展一样,经过局部的实验、实践之后,将诸多成果约定俗成,协同推广,进而成为共同的财产,沉淀为可靠的知识结晶。诗歌言说话语,是对诗歌的“兴观群怨”,只有这样才能克服面对诗歌时的失语状态,才能克服当代诗歌暗夜独行的昏昧状态。这是任重而道远的,有待众人持建设的态度付出努力。

当代诗歌在自身内外取得的巨大成就值得所有人尊重,它本身已成为中国文学、世界文学不可忽视的一个构成板块。像这样反思性的话题还有很多:例如当代诗歌的普及问题,互联网多媒介传播带给诗歌的革新、在工具语言观和本体论语言观之后如何对待语言等等。历史、语境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中骤然迈入了一个新阶段,诗歌亦是如此。很多问题都须重估,我们有信心和热情将诗歌想象成这样一头巨兽:它元气充溢、体魄强健,立在广袤的大地上,又昂首天外,可以自由出入于历史、现实、心灵的一切领域,无所而不往,无往而不复。








发表评论 评论 (1 个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