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言行之辨看文明的兴衰节律
《周易》有云:“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 言行之辨,从来不止于个体修养的范畴,更折射着时代精神的深层脉动。清代思想家颜元在《习学记言》中提出:“天下将治,则人必尚其行;天下将乱,人必尚其言。尚行则笃实之风行焉,尚言则诡诈之风行焉。” 这一论断,将言行的价值取向与治乱兴衰相勾连,揭示出文明演进中一个隐秘而恒定的规律 —— 当人们注重实践时,社会便孕育着笃实的根基;当言辞凌驾于行动之上时,诡诈的阴影已在暗中滋长。这种对 “行” 与 “言” 的深刻洞察,不仅是儒家 “知行合一” 传统的延续,更是对人类文明兴衰周期的哲学总结。

天下将治,则人必尚其行;天下将乱,人必尚其言
一、治世之 “尚行”:笃实之风的生成逻辑
在历史的长卷中,但凡被称为 “治世” 的时代,往往呈现出 “行胜于言” 的集体取向。西周初年,周公制礼作乐,并非空言道德,而是通过 “制为君臣上下之仪,父子兄弟夫妻之节”(《礼记・乐记》),将伦理规范落实为具体的礼仪实践,使 “敬德保民” 的理念渗透于日常起居。春秋时期,子产治郑,“不毁乡校” 却 “铸刑书于鼎”,以制度建设取代空谈,成就 “门不夜关,道不拾遗” 的治世气象。至汉代文景之治,文帝 “弛山泽之禁”“轻徭薄赋”,以务实政策让百姓 “各安其业”,正是 “尚行” 精神的典范。
这种 “尚行” 传统的哲学根基,在于儒家对 “行” 的本体论定位。孔子说:“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将 “行” 视为德性的终极呈现;荀子更直言:“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荀子・儒效》),构建了 “行高于知” 的实践论体系。在治世语境中,“尚行” 意味着价值共识的落地生根:当政治精英以 “修身齐家” 为起点,通过 “治国平天下” 的实践来兑现理想,当普通百姓以 “耕读传家” 为准则,在日用伦常中践行道义,整个社会便形成 “笃实之风” 的良性循环。这种风气的本质,是对 “知行合一” 的集体信守 —— 言辞的价值,唯有通过行动的检验才能成立;社会的秩序,唯有通过脚踏实地的建设才能稳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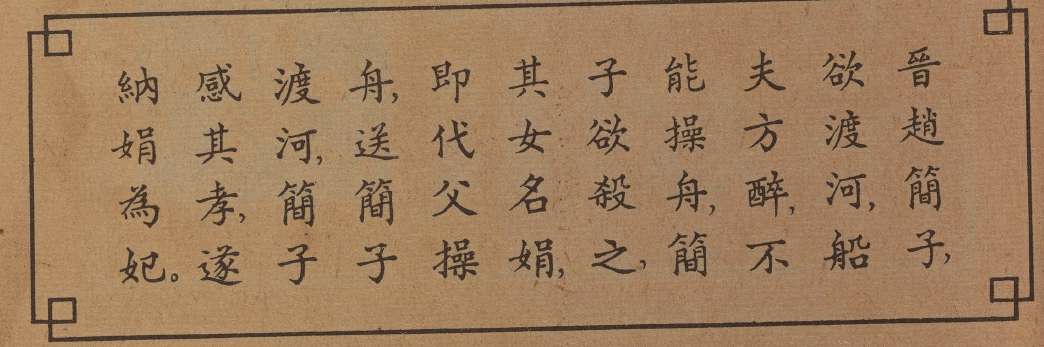
天下将治,则人必尚其行;天下将乱,人必尚其言
二、乱世之 “尚言”:诡诈之风的蔓延轨迹
反观乱世,往往是 “言胜于行” 的时代。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诸子蜂起,《庄子・天下篇》形容此时 “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于是 “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纵横家苏秦、张仪 “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靠三寸不烂之舌翻云覆雨;稷下学宫的辩士们 “饰人之心,易人之意,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庄子・天下》),虽推动思想繁荣,却也埋下 “言伪而辩” 的隐患。魏晋时期,玄风大盛,士人 “祖述老庄,立论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晋书・王衍传》),清谈误国,终致 “五胡乱华” 的乱局。正如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所批判:“刘石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人人知之。”
“尚言” 之所以导致诡诈,在于言辞与实践的割裂。当人们沉迷于概念游戏而忽视现实关怀,当政治沦为权谋家的修辞表演,当道德沦为装点门面的漂亮话,语言便失去了承载真理的功能,异化为权力博弈的工具。韩非子曾尖锐指出:“好辩说而不求其用,滥于文丽而不顾其功者,可亡也”(《韩非子・亡征》),正是对 “尚言” 危害的预警。在乱世语境中,“尚言” 本质上是价值体系的崩解:人们不再相信行动的力量,转而依赖言辞的包装来获取利益;不再追求真实的联结,转而擅长用话术制造幻觉。这种风气的蔓延,如同腐蚀文明根基的酸雨,使 “信” 与 “诚” 的伦理纽带逐渐断裂,最终导致整个社会陷入 “上下相诈,君臣相疑” 的信任危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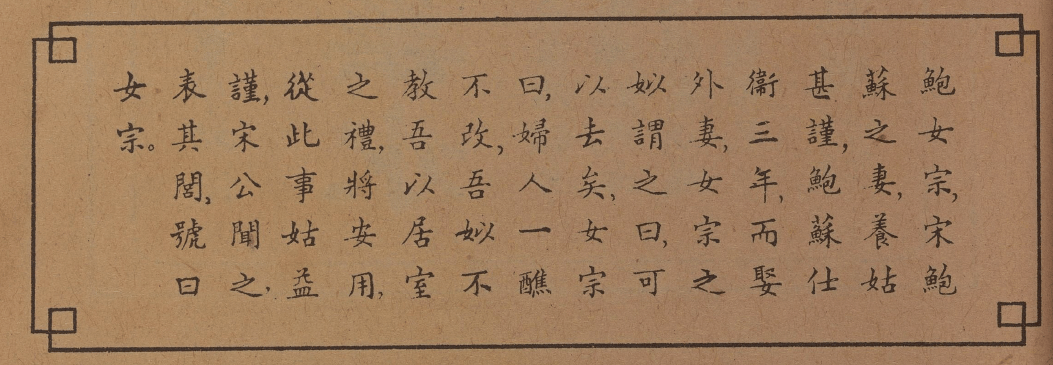
天下将治,则人必尚其行;天下将乱,人必尚其言
三、言行之辨的哲学深层:存在论视域下的实践转向
颜元的命题,不仅是历史经验的总结,更触及哲学的根本问题 ——“存在” 与 “表象” 的关系。在儒家传统中,“行” 代表着对 “存在” 的直接介入,而 “言” 则是对 “存在” 的符号化表达。当 “行” 成为主导,人通过实践与世界建立真实的关联,在 “成己成物” 的过程中实现存在的本质;当 “言” 占据上风,人则沉迷于符号的游戏,在语言的迷宫中遗忘了真实的世界。这种区分,与海德格尔对 “沉沦” 状态的分析异曲同工 —— 当人被 “公众意见”(das Man)所支配,沉迷于 “闲言”(Gerede),便失去了本真的存在方式。
从知行关系的演变看,宋明理学的 “知行合一” 论,正是对 “尚言” 倾向的纠偏。王阳明说:“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传习录》),强调真正的 “知” 必须包含实践的维度,否则便是 “悬空思索” 的伪知。这种思想,与颜元 “习行” 哲学一脉相承 —— 颜元痛斥宋儒 “空谈性命”,主张 “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要求通过 “手格其物” 的实践来体认真理。他们共同揭示了一个真理:人类文明的存续与发展,始终依赖于 “在现实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马克思)来解决问题,任何脱离实践的高谈阔论,终将在历史的淘洗中沦为泡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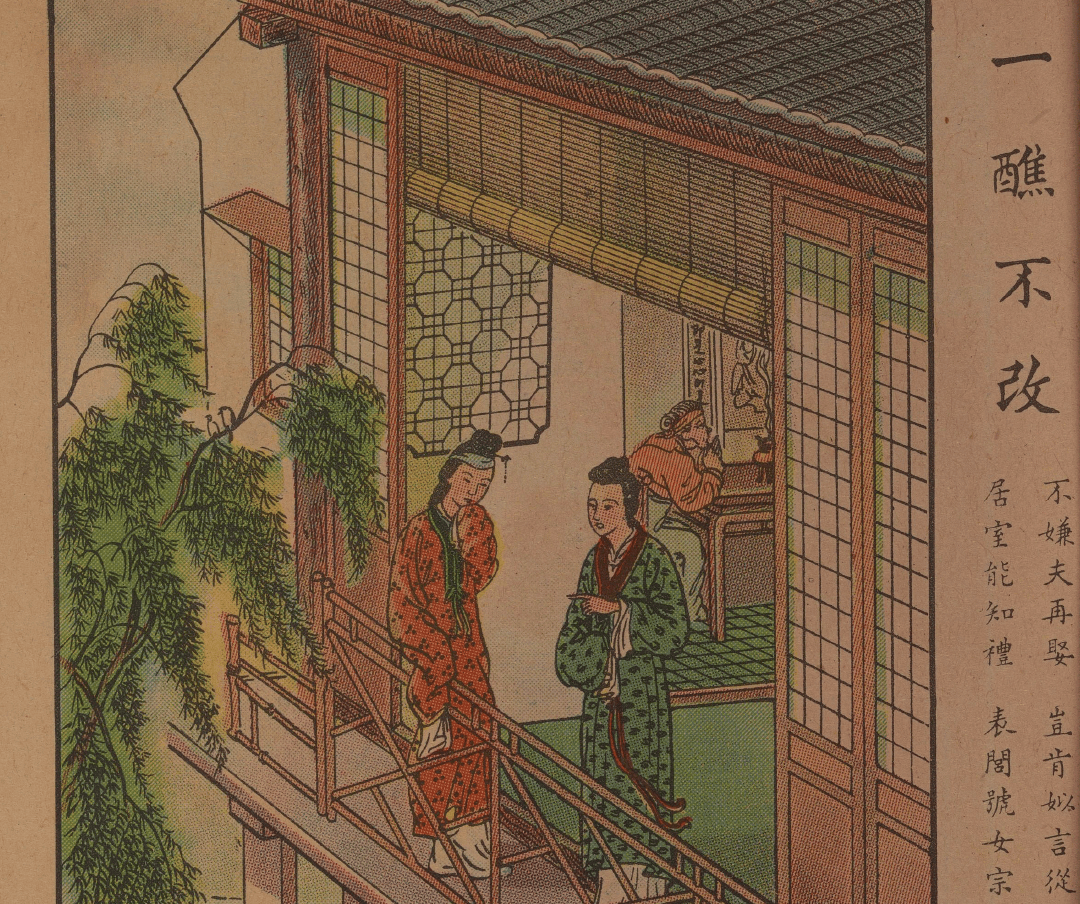
天下将治,则人必尚其行;天下将乱,人必尚其言
四、现代性困境:在言辞膨胀中重拾 “尚行” 精神
在技术革命重塑人类生活的今天,颜元的警示愈发具有现实意义。社交媒体时代,每个人都是 “言论的生产者”,140 字的推特、短视频的文案,构建起一个 “语言过剩” 的世界。学术领域,概念迭代快于思想沉淀;政治领域,修辞术胜过政策实效;商业领域,营销话术掩盖产品本质。正如鲍德里亚所言,我们正生活在一个 “拟像”(Simulacra)的时代,真实与表象的界限日益模糊,“尚言” 的风气以更隐蔽的方式蔓延。
然而,真正推动社会进步的,永远是那些 “沉默的行动者”:袁隆平田间地头的耕耘,屠呦呦实验室里的坚持,航天团队对 “星辰大海” 的脚踏实地。这些 “尚行” 的典范,印证着马克思的论断:“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在文明面临生态危机、价值分裂的当下,唯有回归 “笃实之风”,才能在言辞的喧嚣中重建真实的联结 —— 让学术研究扎根于现实问题,让政治实践指向民生改善,让个体修养落实于日常践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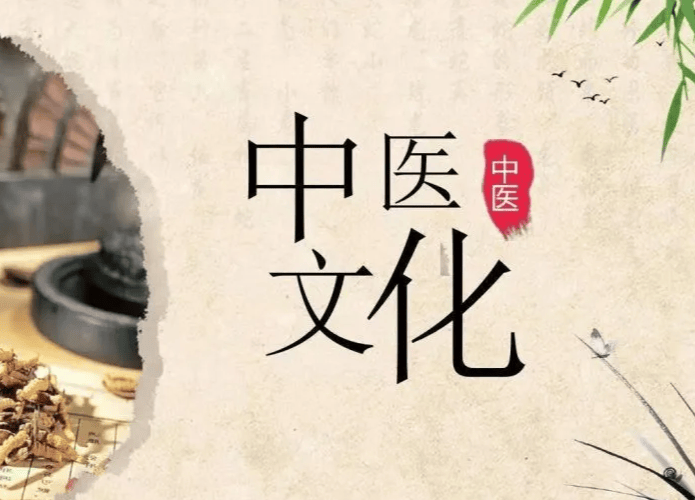
天下将治,则人必尚其行;天下将乱,人必尚其言
在知行循环中守护文明的根基
从西周的 “敬德保民” 到当代的 “真抓实干”,“尚行” 精神始终是文明的压舱石;从战国的 “百家争鸣” 到今天的 “信息爆炸”,“尚言” 的诱惑从未消失。颜元的智慧告诉我们:治乱的关键,不在于言辞的多寡,而在于言行是否统一;文明的兴衰,取决于人们究竟是在 “做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还是在 “讷于言而敏于行” 中默默耕耘。正如《周易》所言:“君子以行过乎恭,丧过乎哀,用过乎俭。” 这种对 “行” 的敬畏,对 “实” 的坚守,才是人类在任何时代都不应丢失的精神基因。
当我们在键盘上敲下无数观点时,不妨想想:真正改变世界的,从来不是言辞的泡沫,而是那些俯身大地的身影。在 “天下将治” 或 “天下将乱” 的历史分野中,每个人的选择 —— 是尚行还是尚言,是笃实还是诡诈 —— 都在为文明的走向投出无声的一票。或许,这正是颜元命题留给我们的终极启示:唯有让行动成为言辞的注脚,才能在时代的长卷上,写下永不褪色的篇章









发表评论 评论 (4 个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