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1990 年代后期, 1970 年代出生一代的艺术开始真正崛起,这就是“ 70
后”艺术。从九十年代末尹朝阳、谢南星等人“青春残酷”绘画的产生,到李继开、欧阳春等人“漫画一代”的崛起,标志着中国当代艺术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即“ 70 后”艺术时期。
“ 70 后”是指 1970 年以后出生的一代。“ 70
后”一代无意中成为市场改变中国之后的一代,他们被历史重新规定了一个本质不同的背景。这个改变意味着市场改变中国之后的一系列改变,即消费主义改变中
国,娱乐文化改变中国,财富分化改变中国,都市化改变中国,全球化改变中国,网络改变中国等等,对于这一代人自我和精神模式的根本改变。
这个改变也带来对这一代人艺术的根本改变。由此,在九十年代末正式拉开了“ 70 后”艺术的序幕。
自我矛盾和挣扎:处在国家上升时期的自我景象
1990 年代所带给“ 70
后”一代的根本变化是消费社会、大众社会和市民社会的形成,它与国家社会主义和后意识形态体制构成一种新的社会总体性。这一代的成长背景是中国一百年来最
强盛和充满活力的十年,意识形态的绝对控制已经解体,全球文化和跨国公司的进入中国,消费品在大型超级市场的货架上比比皆是,性开放、电子游戏、动漫文化
和海外流行文化的大规模入侵,都市化、商业文化、有线电视、互联网逐渐消灭了南北文化差异和中心城市和边远城市之间的地方性,等等。
这一代处于国家经济上升以及社会生活相对开放的时期,但这一进程同时也伴随着痛苦的道德挣扎、残酷的社会竞争和自我精神的物化。 1990
年代的中国是一个繁荣和衰败共生、希望和挣扎共存的年代,它充满进步的粗放性力量,令人新奇和想象;它也因为旧道德秩序的加速崩溃和新的阶层分化,使这一
代在青春期开始就陷入一种上一代从未有过的自我矛盾和挣扎。
“ 70
后”艺术不可避免地反映出这个国家处于上升时期的自我景象。对于城市和社会的资本主义方式的闯入,最初反映在生活在广东阳江的郑国谷的摄影中,而不是首先
出现在北京、上海的新艺术中。郑国谷的阳江代表着一个想象性的中国小城的现代化寓言,这个原来处于前现代化的南方小城,在一夜之间有了麦当劳、有线电视、
盗版光盘、好莱坞电影、香港歌曲、韩国电视剧、日本漫画,一群群白领,以及他们和很多都市青年相似的白领生活。郑国谷提供了一个九十年代市民社会形成新的
总体性样本,他后来的《东京上空的故事》、《阳江青年的生活和梦想》,都不再是像上一代那样对于社会的落后面进行现实批判,而实际上开始反映这一时期中国
社会生活和城市景象出现的新变化,即物质消费和市民社会的自由性的出现,在郑国谷的作品中既表现出一种现代化认同,也隐含一种自我感伤色彩。后一种感受来
自这种新的进步变化同时伴随的残酷的社会进程,对“ 70 后”一代纯真的青春想象的摧毁。
这种复杂的自我态度稍后几年也本能地出现在崔岫闻关于北京夜总会女洗手间的纪实录像中。崔岫闻的录像采用了与郑国谷相似的截取社会样本的方式,但呈现
的社会纪录要比郑国谷的阳江社会表面更触目惊心。她窥探了一群与她同龄的女青年在北京一家夜总会洗手间的私密生活,这些青年女性拼命地化妆、与性追求者电
话周旋、紧张地数钱等。崔岫闻的录像没有直接体现性交易在九十年代经济成长中的重要角色和广阔的社会背景,而是体现出一种直接录像风格的洗手间内的“战
场”气息,她在录像中没有直接的社会评价,而是主要体现出一种先锋的女性主义态度。
对于“ 70 后”一代的自我内在性开始准确刻画的是以尹朝阳和谢南星为代表的“青春残酷绘画”的先声夺人的登场。“青春残酷绘画”也标志着“ 70
后”一代的目光从对社会表象繁荣的新奇和这层社会表象底下的残酷现实,开始转向自我内心表象的呈现;同时,也标志着“ 70
后”艺术的自我特征在整体上真正成形,并在艺术观念、图像方式、美学风格和视觉趣味上真正与上一代拉开差距。
“阳光下的感伤男孩”和“梦魇中的分裂男孩”在 1998 年前后几乎同时在尹朝阳和谢南星的笔下诞生,成为“ 70
后”一代标志性的自我形象。尹朝阳表现了“ 70
后”自我形象的外在表象,他们在阳光下忧郁而略带感伤,表情矛盾而痛楚,心情复杂而忐忑不安,光着膀子站在北方的阳光下,看着不确定的远方。谢南星则表现
了“ 70 后”自我形象的内在表象,那些男孩痛苦、焦虑、神经质、甚至有点癫狂和自我分裂,面对一个有点血腥和人性黑暗的封闭空间。
“青春残酷绘画”在尹朝阳和谢南星那里,表现出在社会性和自我特征上建立了一种完全属于“ 70
后”艺术自己的形象模式。这个形象模式后来为越来越多的“ 70 后”艺术家所认同,并在摄影、绘画和雕塑等方面逐渐形成“ 70
后”艺术自己的形象谱系。“阳光下的感伤男孩”和“梦魇中的分裂男孩”实际上是一个道德模糊和自我不确定的形象,这个模式反映在画面上就是社会现实背景的
消失,使得这种形象表现为一种以写实表象方式呈现的寓言性自我,它不是一个现实的形象,而是一个关于内心的寓言表象。这事实上也开辟了“ 70
后”艺术对于寓言表现方式的信心。
这两个男孩形象的另一个重要意义,在于“ 70
后”群体正式形成了有别于上一代的道德和社会态度,即他们所处的时代没有什么可能是完全对的,也没有什么是完全错的。他们的痛苦来自社会系统的缺陷,但这
种缺陷由于在 1990 年代的民族主义进步的集体要求又被认定为是一种正当性缺陷。因此,“ 70
后”一代并不能明确导致他们痛苦的直接所致的根源和敌人是什么,他们的一切青春痛苦并不像 1980
年代那样可以有一个直接的制度可以攻击和反弹。这个态度的另一个标志性形象也在杨福东的表演摄影《最后一个知识分子》中得到了明确的表示。
在这样一个后意识形态的道德和社会背景下,“ 70 后”一代的艺术在精神表达的本质上实际上是一种寓言性的自我表现,以及在美学上的自我避难。
自我寓言:从青春残酷到想象自我
“ 70 后”一代成长于 1990 年代,这个十年实际上也是消费社会在中国的形成过程。长在消费社会这一背景下,几乎使“ 70
后”一代的艺术从现实自我、想象性的自我一直到虚拟的自我,从社会空间、私人空间一直到想象性的寓言空间和虚拟空间,都具有这代人在 1990
年代中后期呈现出的对于消费社会的一种个人感受和自我想象,并创造了比上一代更为丰富和更具想象力的自我形象。
在郑国谷和崔岫闻的作品里,可以从社会和都市表层,一直到内部和私人空间,找到消费社会无所不在的存在,以及在某些空间的残酷性和感伤色彩。处于中国
南方的广东是中国消费社会文化最初形成的地区,因此,在 1990 年代中后期开始涌现出一批表现消费社会文化对“ 70
后”一代产生影响的艺术家,像杨帆、曹斐、杨勇、蒋志等人,紧接着在各地的“ 70
后”艺术更是大规模转向一种表演性和寓言性的视觉方式,来表现这一代人正经历着的内心残酷,像何岸、陈秋林、刘瑾等。
何岸的《关于时尚的十五个理由》系列采用电脑技术在“都市酷女孩”身上虚拟一条伤疤,成为“ 70
后”青春残酷主题在观念摄影方面的标志性形象。“都市酷女孩”在 1990 年代后期一直为许多“ 70
后”艺术家作为表现的主要形象,在趣味上开始追求与国际流行潮流的“酷”视觉,“酷”实际上也正式成为“ 70 后”群体的美学倾向。杨帆在 1990
年代末开始表现南方打工妹将自己装扮成时髦女性但仍然未脱尽乡土气息的形象,通过对她们被消费文化重新塑造的女性表象,反映了新一代在经济浪潮中的去地方
性过程,并体现出对这一代青年女性的纯朴自我和地方性被大众流行文化消灭的感伤情绪。
这种“都市酷女孩”形象在杨勇和陈秋林的作品中被内在赋予了一种虚无性的青春经验。杨勇的《青春残酷日记》系列中表现的是生活相对优越的深圳白领和酷
女孩的都市虚无感。她镜头下的“都市酷女孩”也开始呈现出一种国际都市气质,以及物质社会中非主流青年的自我空洞的迷幻状态。陈秋林的表演摄影《无题》也
表现了穿着婚纱的都市女孩在四川的工业背景下的虚无感,她的 Video 《废墟》则表达了对于山城小镇被城市拆迁的感伤。
曹斐的 Video
和蒋志的摄影则试图超越对于都市化和社会残酷的快速变化对于纯真青春的自我打击经验的一般性呈现,而是深入到一种存在主义的荒诞感的表达。曹斐的
Video
类似于一种寓言表演情节剧,她的《链》、《狗》等作品表现了一种极度压抑的都市生活的日常性。蒋志的《屉中物》和《吸管人》系列采用了一种非常戏剧性的表
演摄影,表现了一种自我封闭的日常压抑感和人生游戏感。刘瑾利用了经典新闻摄影的图像,将其篡改成虚构的青春社会戏剧现场,来表达自我的成长情景。
以秦琦、陈延辉、李大方为代表的东北新生代绘画呈现了“ 70 后”艺术的一种叙事性绘画的前卫风格,体现出“ 70
后”群体在绘画的图像观念和叙事性方面的学院派实验。他们的绘画一直以图像的叙事实验作为载体,表现东北后现代社会风格下的自我成长经验。秦琦的《处理
器》和《小马》表现了一种想象性的自我冥想,以及一种荒诞而自娱性的奇异的自我经验。李大方的《凶险》和《激动的解释》等建构了一个想象性的戏剧瞬间,这
种视觉经验试图建立一种现实和虚构的同构特征,保持画面指向的一种到底是现实还是想象的模糊性。同时,他还试图使图像情节处于一种只有现在时刻的激情和张
力,却没有前因后果的“中段”状态,或者前因后果的不确定性。陈延辉的《愿意收留》、《她不停地叫》等试图在一个缺乏社会高潮和运动的时代制造一种神经质
气质的想象性癫狂,他的题材涉及同性恋、精神病、科幻凶杀等反常经验的自我呈现,侧重于一种个人化的病态实验。
李大方、秦琦、陈延辉等人的绘画实际上反映“青春残酷绘画”之后,“ 70
后”艺术朝向一种不再直接呈现“青春残酷”的趋向,而是转向围绕着自我表达为核心,将自我经验做成一种形式,建立一个想象性和虚构性参与的自成一体的视觉
表壳,这个壳反映“ 70 后”群体在共同的消费社会和流行文化总体性下的自我世界,也表明“ 70
后”群体在意识形态上并没有类似上一代那样的历史和形而上的参照系。这个群体以自我参照为核心,将自我经验转化成寓言形式,成为他们的一种核心视觉方式。
“ 70
后”艺术所造就的形象,实际上是介于想象界和现实界之间的一种虚构界,这种方式不仅仅是为了表达自我绝望和痛苦,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一种避难方式和致幻方
式。后一种视觉价值在“漫画一代”的视觉方式中体现得更为彻底。
“青春残酷”向艺术自体的寓言性转化还体现在彭禹 /
孙原的结合装置和多媒体的行为表演。他们的表演总是设置一个极其残酷的现场,比如《追杀灵魂》、《犬勿近——论战模式》使用了各种动物现场,《争霸》则设
置了一个具有社会寓言性的三人拳击。彭禹 / 孙原的作品具有一种富有激情的社会现场社会感,直接再现他们青春体验中极端的社会残酷记忆。
当然,在“ 70
后”群体中也不是完全没有形而上和历史的视觉方式,比如管勇和陈波的绘画。管勇的绘画主题像《经典》系列,接近于一种与自我灵魂和宗教的想象性对话,探讨
崇高和知识分子性的衰败导致的自我黑暗和心灵向上的不可能性。陈波的绘画则是借助一种历史超验的方式,对于上一代的集体景观和精神场进行隔代的想象性重
构。他重新描绘了北大荒和五、六十年代的现实,以及那一现实制造的影像,重构他们的灰色人生和乌托邦的精神评价,比如《英雄人物》、《纯真年代》等。“
70
后”对于历史和形而上的关注仍然类似于一种精神的“中段”状态,即他们在市场改变中国之后,也实际上与知识分子的历史性和形而上性发生了大规模断裂,进入
一种与自我历史和经验本能的对话。随着这种自我揭示的深入和逐渐清晰,“ 70
后”无可避免地要进入一种历史和形而上的想象性缺失的探访。实质上,其背后仍然反映一个消费社会和大众社会的形成带给“ 70 后”一代的想象性规定。
“ 70 后”艺术中自我经验的痛苦和绝望感,初期主要体现在青春残酷的主题形象,但这一形象一开始仅仅局限于现实形象的一般化呈现。而后,“ 70
后”艺术开始向内心形象的寓言性和表演性语言转变,逐渐抛弃了对于现实图像的直接使用,以及对于具体成长经验的表达,而进入更抽象的自我特征的捕捉和典型
情景的概括。这是“ 70 后”一代自我形象表现的第一个阶段。
从 1990 年代后期以来,自我形象的残酷性和青春性实际上逐渐从“ 70
后”一代很多人的作品中淡出,开始更个人化、更主观化的个人世界和想象性自我的表现,这体现在尹朝阳、谢南星、崔岫闻、秦琦、陈延辉、李大方等人的近期作
品。这体现了 1970
年代中前期出生的群体在九十年代前期的青春成长,正好是中国社会急剧变化和极端现实的时期。在经过青春苦闷的表达、自我寓言的塑造之后,开始寻求与历史和
超验世界的对话。像李 日 韦 的“自由度”系列摄影,表现了一种“
70后”艺术的新倾向,视觉上不再单纯表现痛苦和压抑,而是表现一种在当代中国个人存在的超验性想象。
漫画一代:“新”的痛苦以及视觉上瘾
在近年崛起的“漫画一代”群体体现出一种更强烈的视觉上的超验性和致幻性。这个群体包括李继开、欧阳春、徐毛毛、俸正泉、熊宇、周文中、刘兵、方亦
秀、 高瑀 等人。“漫画一代”的创作是继“青春残酷绘画”之后又一个重要的新前卫艺术潮流,也是“ 70
后”艺术的一个新的方向性突破。它的出现与日本村上隆等人的漫画艺术在国际上的崛起相差不过五年左右,这个群体的崛起并没有直接受到日本漫画艺术的影响,
它主要扎根在这一代经过十年形成的大众漫画的基础之上。
“漫画一代”群体的年龄层基本上出生在 1970
年代中后期,他们这一代生长在一个好莱坞动画片和日本漫画入侵中国的时刻。在中国成人社会被卷入经济增长进程,试图重新进行财富和社会权力角逐以及生存竞
争时,“漫画一代”以向漫画的超验和致幻世界致敬的方式寻找到一个属于这一代人自己的世界。这个转向也使“ 70
后”艺术真正意义上将这一代的自我寻找走到了极致,在视觉观念和绘画性等方面建立了一套自我语言体系,并真正成为面向未来一代的艺术。
在漫画性这一点上,“漫画一代”找到了不重复西方油画的绘画原创性基础。而在漫画形象的自我内在性上,则具有一种“ 70
后”一代在国家上升时期的自我气质和意识形态特征。“漫画一代”在视觉风格上,开始具有一种安静、细腻的物质社会的自我安逸气息,同时也具有一种微妙的痛
苦感。李继开的《在高处》、《清空日》、《呕吐日》、《利刃》等系列,都反映了这样一种 1970
年代中后期生一代人的虚拟形象,即他们聪明、细腻、善良、物质化、痛苦、压抑、脆弱、自我幻想和恐惧社会,沉醉于迷幻的虚构世界和形象的游戏快感。
李继开的绘画塑造了在红旗下做白日梦长大一代的自我痛苦,他的漫画小人开拓了“ 70
后”艺术一种“新”的痛苦经验及其表现方式,比如渺小、在高空、呕吐以及自杀感,与“青春残酷绘画”不同的是,漫画一代的自我痛苦感几乎是与形象的视觉快
感同时存在。
欧阳春是漫画一代的早期实践者,他在 1990
年代中期就开始尝试以漫画图像作为一种新的绘画性实验,其早期的“匪军”系列是将抗战时期的“伪军”形象和战争现场电子游戏化,而其《稻草人》、《巫
婆》、《恶作剧》则尝试将表现主义的油画笔触与漫画性相结合。欧阳春的“匪军”形象体现了历史在新一代心目中的游戏化和文本化,以及形象的隔代遗传所带来
的内在庄严性的消失。
与欧阳春对于“伪军”形象的重新改造相似的方式,
高瑀也对传统的“熊猫”形象进行了新的视觉解释。熊猫无疑成为高瑀这一代的变体,他们热爱中国传统、幻想爱情、吵架、面对无间道的现实、小资情调等。俸正
泉的《我的山水》则像是这一代的美学宣言,传统的山水具有一种迪斯尼公园式的卡通感,而这座属于“
70后”的山上,则是一切让人舒服和快感的商品和形象。俸正泉表现了一种形象的消费性在“漫画一代”中的视觉本质。
刘兵的绘画系列“为道具而生的小人”类似于一种电子游戏的空间布局和可以被操纵的小人物社会。他塑造了一种新一代的空间隐喻,及其对于世界观的虚拟演
绎。刘兵塑造了一个由各种仪规化的道路、建筑和人物队列构成的有点像电子游戏场景的权力场,这个权力场的表象类似于一个对现实重新组合的未来社会空间,它
表面有序但各个角落弥漫不正常气息,到处充斥着拿着利刃的精神反常者,他们或者虚幻地钓鱼,或者举止诡异。
痴迷漫画的新一代
成长于一个精英文化衰败的年代,这一代也是独生子女的一代,他们跟中国任何上一代人的成长环境和模式都不一样。他们不再像上一代那样被从小教诲成为一个伟
大的人并去改造世界拯救他人,他们成长在一个国家上升复兴的时代,他们比上一代享有更多的物质享受和流行消费,使自己快乐并善意地对待别人,一个人自得其
乐,从小被隔绝在家庭和学校的受鼓励和善待的理想氛围里,不知道现实世界有多么残酷和邪恶,一踏进社会就容易脆弱和受伤,几乎是这一代人自我成长形成的精
神特征。这种特征在熊宇的画面中具有一种寓言化形象。他的穿皮衣的卡通人在透明的水池中的虚无感,体现出在物质消费中成长的这一代的脆弱、敏感、幻想、自
我中心以及精神飘浮的社会性特征,即他们是养尊处优、灵魂漫无边际的一代。
手拿利刃、血以及虚无感几乎是在很多漫画艺术中表现出一种虚拟的残酷,但又不是很现实的那种残酷,而是一种没有切肤之痛的很酷和很快感的痛。这种痛苦
感在“ 70
后”艺术中初见端倪,但在漫画艺术一代中表现得更彻底,也几乎是一种更奇特的上一代人所没有的经验,即形象的痛苦感和漫画性的愉悦感几乎一起涌现,精神现
实的虚无感与漫画世界的超验快感相互融合,画面弥漫一种海洛因式的视觉上瘾性。这也表现在周文中的《花园游戏》系列中,他的作品表现了一种虚拟的暴虐和游
戏的暴力感,体现出这一代内在压抑的超验性表达方式。
“漫画一代”在绘画的图像经验上真正找到了一种自我基础,即这种精英的视觉经验是以对于这种图像的视觉快感为基础的。其视觉经验与本土的当代大众文化
也具有直接的同步性,尽管这种大众漫画文化本身也是外来的。
“ 70 后”艺术有没有一种七十年代性?
“ 70
后”一代的成长实际上适逢中国一千年以来从未有过国家体系和社会文化格局。一方面,这个国家已经对全球资本主义开放,使它具有国际性经验;另一方面,这个
国家还未对资本主义和西方意识形态完全开放,还具有相对的中国性。这种双重性使这一代被赋予了一种新的自我总体性。
“ 70
后”一代因为市场改变中国而使他们有机会表现这一急速地变化,以及这种高速变动社会带给年轻一代的自我冲击。这在表现内容上确实是历史背景的转换带给这一
代的新特质。这本身也反映了“ 70 后”艺术仍然在于一种外在的社会塑造,并不完全是这一代人主动的思想和反省产生的新思潮。事实上,“ 70
后”艺术的七十年代性主要在于自我形象和文化背景上的代际特征,他们更多的是面向自我的社会性,以及毫无历史和形而上对话的自我想象。
“ 70 后”艺术主要反映一种自我和社会的变化,并未像 1990
年代前期那样回到艺术内在性的实践,但事实上,那个阶段也已经接近不可能延续的终结状态。“ 70 后”艺术实际上面临着“八五新潮”到 1990
年代中期“现代艺术”在中国实践的最后困境。一方面,“现代艺术”与十九世纪以前的中国艺术传统在内在性上被证明无法打通;另一方面,反叛意识形态的模式
也不再可能。
不能说“ 70
后”一代如何自觉站在一个新的位置上寻找当代艺术的未来,但他们在社会性的自我表现和艺术观念的实践上,得确本能地开始了一种新的方式和倾向。这表现在“
70
后”一代确实不再关心与西方艺术史的关系,也不太关心社会批判和知识分子式的崇高角度。他们一开始就很专注于自我的表达,并从自己的成长经验中寻求适合这
种表达和美学避难价值的视觉形式。这一方式使“ 70 后”艺术的语言几乎大规模地采用了寓言性和表演性的方式,在手段上,使用了大量的新媒体、摄影、
Flash 动画以及计算机媒介。
在形式的寻求上,“ 70 后”艺术也很少从纯艺术的角度进行内在性的先锋实验,而是强调一种自我形式。事实上,“ 70
后”艺术的先锋实验在绘画的图像和叙事性、新媒体动画以及女性主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实践。
在“ 70
后”绘画中,尹朝阳、谢南星等人的“青春残酷绘画”对于图像摄影性的吸收,李继开、欧阳春、方亦秀、徐毛毛等人对大众文化漫画视觉的图像吸收,以及秦琦、
李大方、陈延辉对于图像叙事性的实验,后者近期的绘画实验主要在于模拟一种超验的现实,像李大方的《扎西》、《渔人》,秦琦的《请你小心点》,陈延辉的
《在别处》等,都是 1990 年代后期在绘画性方面的重要图像实验。
“漫画一代”对于图像漫画性的吸收,也解决了对于西方绘画图像和笔触的模仿性,并在绘画性上迈出了原创性步伐。像方亦秀、徐毛毛等人在漫画的构图和形
象方面已经具有一种超越大众漫画的图像原创性。漫画性的实践还包括 Flash 动画和雕塑方面的先锋实践,像 Flash
动画的早期实践者蒋建秋创作的“强盗天堂”、《新长征路上的摇滚》、《红先生》;汤延、郭泽洪、何岸等人的卡通漫画风格的雕塑,都体现出“ 70
后”艺术在 1990 年代末一直试图将漫画性引入前卫艺术实践。
“ 70 后”艺术的另一个重要现象是女性先锋艺术群体的真正崛起,像崔岫闻、陈羚羊、曹斐、陈秋林、沈娜、唐洁渝、韩娅娟、刘非等人。“ 70
后”一代的女性艺术家在观念性、新媒体、精神极端性、同性恋题材等方面都真正意义的将女性艺术推向了先锋艺术实践。崔岫闻在《洗手间》之后创作的《三
界》、《 2004 年的一天》等系列,不仅代表了女性艺术,也是“ 70 后”艺术的观念艺术的代表作品。
陈羚羊的《十二月花》系列则是一种极端的女性自我实验,体现了女性先锋艺术早期的“残酷”风格。沈娜的《右手》系列等大胆尝试了漫画视觉的女同性恋形
象,这也是“ 70
后”艺术最先尝试的女性形象。唐洁渝的绘画图像类似于一种介于魔幻和漫画之间的超验视觉,隐喻着一种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新一代俯瞰现实的魔幻视角。韩娅娟、
刘非则在摄影和 Video 方面体现出了一种“ 70 后”一代女性的在物质社会的自我感觉。
“ 70 后”一代是一个已经形成的艺术思潮和群体吗?恐怕奉行自我和独立性的这一代都不会轻易承认这一点,并且被简单归类。但事实上,“ 70
后”的七十年代性作为一个共同的集体成长背景还是存在的。他们因为市场改变中国之后而成为与上一代自我关系断裂的一代,并且这一代都几乎在一个遗忘历史的
精神前提下重起炉灶地形成新的自我模式。
“ 70
后”艺术的核心意义在于,这一代的艺术真正回到艺术本身的自体性,并开始将自我表达和本土生活的呈现作为一种基本方向,而不是像上一代那样考虑与西方艺术
的竞争为核心。“ 70 后”艺术在绘画性、新媒体、 Flash 动画、漫画视觉等方面建立起自己视觉语言,并在艺术观念和视觉形式上正在超越
1990
年代艺术。但这一代在享受国家上升带来艺术复兴的可能时,也不可避免的要接受这一代的宿命性和悲剧性,即他们享受了物质、开放和跨国资本主义,以及相对的
繁荣和自由;却同时失去了像上一代那样享受对于历史和形而上的亲近和自我拯救。
2005 年 5 月 23 日完稿于上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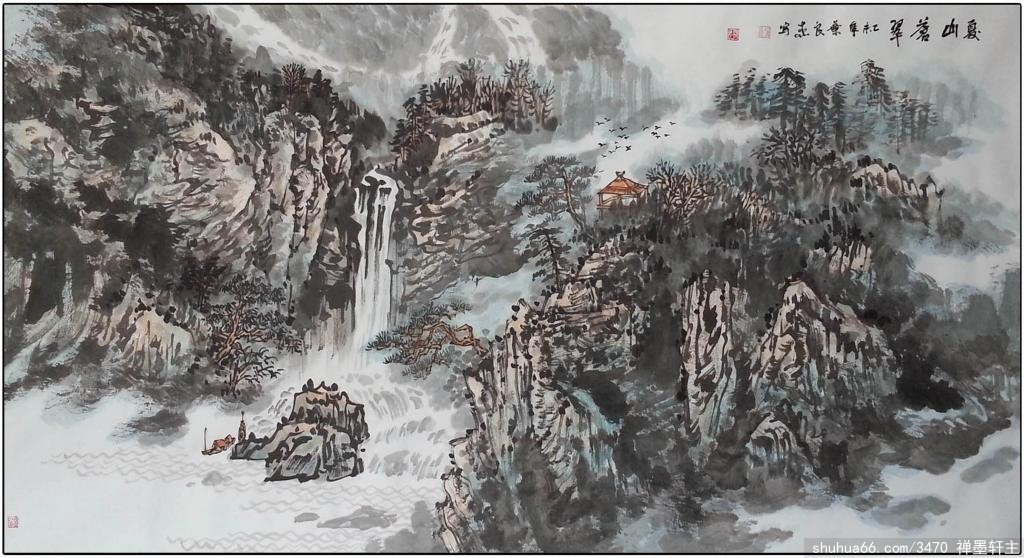












发表评论 评论 (4 个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