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是中国现代女作家萧红开启创作生涯90周年。1933年,萧红以笔名“悄吟”踏入文坛。她先后出版《生死场》《呼兰河传》等多部作品,被称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文学洛神”。90年间,尽管文坛内外对这位天才写作者的评价不一,但无可争议的是,她在那个时代堪称独特。
回顾萧红的一生,她曾十九岁离家出走,随后告别故乡开启了十数年的漂泊。某种意义而言,萧红自己的故事本身就是太过精彩的小说,但她并没有去书写,而选择把一切归还给生命,同辈中很难有作家能够抵挡这样的诱惑。北京大学教授戴锦华曾在《浮出历史地表》中对萧红其人其文赞许有加,时隔三十余年,她会如何看待此前作出的相关评价?以及在今天,当我们试图重新讲述萧红的一生时,其中的难点又在于什么?
值萧红创作生涯九十周年纪念之际,译林出版社推出函盒纪念版“萧红作品:她和她的黄金时代”。值此之际,新京报书评周刊·文化客厅联合译林出版社、中国建投集团建投书局,邀请北京大学教授戴锦华、青年作家格子围绕上述问题展开交流。本文为对谈整理,内容有删改。

“萧红作品:她和她的黄金时代”函盒纪念版
1
双重叙述下的萧红:
萧红的创作比她的生命更加广阔深邃
格子:我简单介绍一下萧红,她是一位生命非常短暂,但一生非常华丽的作家。她1911年出生,在自己22岁那年,以笔名“悄吟”开始写作,在23岁左右就创作出了著名的《生死场》,但非常可惜,她31岁就因一次误诊病逝于香港。
萧红从1933年开始写作,到现在走过了90年。这90年间,人们对萧红的评价其实经历了非常大的变化。尽管鲁迅对她的评价很高,说她最有前途,但那也是对潜力新星的评价。到后来,有声音认为她独特但不成熟。到今天我们可以说,在她同时代的作家中她是“一枝独红”。那么戴老师,您是如何看待萧红这一生的呢?
戴锦华:萧红无论作为文学,还是作为历史,作为女性的历史、女性的生命都堪称一个奇迹。活到我这个年龄来看,31岁真的很年轻,甚至生命还没有真正铺陈开来。我最早读到萧红的《呼兰河传》,感受到一种巨大的冲击与震撼。我认为,今天我们所说的女性或者叫新女性,其实是五四运动的一大发明,我们实际上在一个东西方文化的撞击当中,大致接受了西方的性别想象,来创造了这样一个判然有别的两性概念。所以新女性曾经是一个非常年轻的社会角色。而现代汉语也是一种新语言,也是从胡适先生的白话文运动才开启的。两种新的叠加,就使得今天我们回看五四一代人的时候,觉得他们年轻、幼稚。
但是我第一次遇到萧红的时候,我感觉到的是某种沉郁,某种生命的伤痛与强烈的对生命、对世界的爱所形成的厚度。她没有同时代绝大多数女性的自我设限,她也没有那个时代女性在语言文字或情感表达上的幼稚。
格子:当我看到她在文学史上经常作为群像之一被呈现时,我有点不甘。您觉得她的地位该被单独设章吗?或者说目前以群像讨论萧红的现状,未来会有所改变吗?
戴锦华:没法判断,但至少我希望改变。不论从她所属的东北流亡作家群,还是30年代女性作家群而言,她都非常独特,甚至可以说达到了某种高度。
格子:34年前,您曾在《浮出历史地表》中从女性主义角度评价萧红的作品。时隔多年,您如何回看当时做出的评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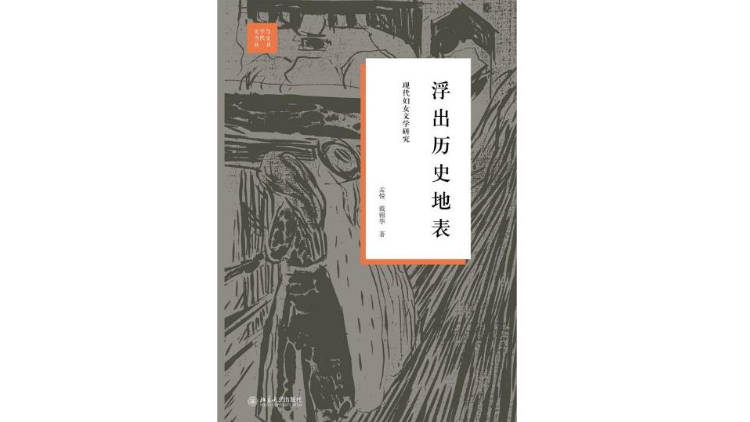
《浮出历史地表》,孟悦 / 戴锦华 著,培文|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年5月。
戴锦华:如今回看,我会觉得当时我因为刻意想从性别维度出发,反而没能更好地把握。萧红其实一直在双重叙述当中,一重是她自己的作品所形成的叙述,文学是历史的,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一块土地和一个时代的叙述;而另一重就是她个人的生命故事。绝大多数作家的个人生命就是他(她)们创作的底本,而萧红的创作明显比她的生命要更加广阔深邃,但这并不意味着她的生命故事就没有价值和意义。我们如何把这两个部分融合成完整的故事?她既是大时代的儿女,也是一个从旧时代中建立新舞台的女人。
格子:萧红的一生其实是在非常撕扯的环境中度过的。生活中既有让她非常寒心的父亲,也有温暖的祖父。而萧红本人的经历也非常曲折,她曾“三次被抛弃”。戴老师,您觉得萧红一生坎坷的经历,对她的创作是一种助益吗?
戴锦华:在中国的文学史当中,我们确实经常遭遇到一种天才少女,不是因为她们经历了生活的坎坷和磨难,也不是她们学习或者思考达到了某种程度,而是她们好像就是直觉式的书写,却写出了很多大师都达不到的高度。
要理解萧红,其实离不开东北的历史、近现代中国的历史。从这个意义而言,萧红个人故事中的曲折,其中的传奇性或者绯闻性相对来说是可求解的,反而是她作品所触碰的那段历史,远非经由她的个人故事便能穷尽的。换句话说,萧红自己的故事本身就是太过精彩的小说,但她并没有去书写,她把这个留给了自己的生命,可能很难有作家能够逃过这样的诱惑。同时,这也是我们观察女性作家时存在的视差,我们可能更多关心她的生命故事、她的爱恨悲欢,而没有去看她所背负的时代,那背后更宏大的历史。

活动现场。(出版社供图)
2
无意识进入的现代写作:
萧红的语言幼稚吗?
格子:接下来聊聊萧红的写作。萧红的作品大约成稿于近百年前的白话文运动期间,如今,有部分学者认为萧红的语言在今天看来有些幼稚,戴老师如何看待这样的观点?
戴锦华:首先需要坦白的是,我的专业主要在电影领域,并没有及时阅读文学研究方向的最新论文,我个人并没有读到这样的观点。说回“新语言”,在许多场合我曾多次提过,五四那一代人的语言是新语言没错,但我认为胡适先生是自己给自己自觉编织了一个关于白话文运动合法性的故事。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胡适先生自己是中国白话文文学的作者,而在现代汉语出现以前,国民一直在使用文言文或古白话文书写。今天我们如果较真,会发现很多古白话文作品,比如《水浒传》《红楼梦》,其实比很多现代作家的汉语作品读来更加流畅。
但胡适等人提出要口语化,问题并不在于读感,而是现代汉语的创造本身就是中国最为深刻的文化现代化过程。归根结底,现代化是一次发明,现代汉语看似是古汉语的延续,实则遣词造句都是内置于现代化的更替逻辑,在现代价值的系统当中。因此,五四一代人开始使用由他们创造出来的新语言写作时,势必是生涩且别扭的。文学是语言的艺术,那一代作家要先创造语言,再使之成为艺术,这不是所有人都能达到的。因此今天的我们会觉得他们的作品文白夹杂,不够流畅,其实这种批评是反历史的。有他们才有今天的我们,才有如今越来越成熟的语言系统。
即便如此,萧红的语言成就依然大大高于其同辈。她克服了现代汉语的生涩,找到了一种偏朴素的叙事方式,这使得她绕过了一些陷阱,以及一些难以突破的时代局限。其实萧红的文字并不朴素,毋宁说它是一种准确。坦白说,我在表达时都难以避免要借助形容词,但萧红的作品不是,她更倾向于使用名词或动词直接表述,她赋予了文字以流动性。如果说这样的文字是幼稚的,那什么是成熟呢?
格子:的确,在很长时间里,新闻写作一直在尝试一种更加现代的方式,短句为主、简洁准确。从这点而言,萧红近乎无意识地率先进入了一种现代写作,她的文本大多两三行成段,节奏明快,但表达的意思并不简单。从这个角度而言,萧红恰恰超前于时代,而她自身又并非全然有意识。这使得她的作品有一种更大的阐释空间,我们是否可以说这也是萧红作品的迷人处之一?
戴锦华:毫无疑问(是这样的)。说不尽的东北、说不尽的沦陷时代、说不尽的中国曾全面遭受挣扎图存的困局、或者说不尽的女性与文学,所有这些都可能成为我们再度进入萧红的路径,这也是她在同时代作家中脱颖而出的重要原因。
3
“半部红楼”,
是一部具体的作品吗?
格子:我想谈一点我的阅读感受。我是山东人,我的半个家族都在萧红离开东北的那个年代进入了东北。甚至当我们今天说起东北文艺复兴时,我常常以为要复兴山东的文学。这么多年,在家族口述史中,我听到的故事和萧红笔下的故事视角完全不同,我始终无法想象当年的族人们在东北感受到的是怎样的土地,而这些都是我从《呼兰河传》和《生死场》中读来的。最开始阅读萧红时,我只是“试图在看”,就像有一阵子我看知青文学,是为了看懂我妈妈是如何成长起来的。文学很多时候带我们体验无法亲历的过去,但在情感上又非常需要进入其中。
另外,前一阵子我在飞机上读了萧红的另一部作品《马伯乐》,这部作品的冲击太大了,以至于萧红在弥留之际都非常遗憾自己没能力真正把它写完。我就在想,萧红在弥留之际的时候说,她曾经开启过半部“红楼”,但她很遗憾,这个只能由后人来书写了。在您看来,首先,这半部“红楼”是不是《马伯乐》?其次,在萧红短暂的人生最后,她是否有再开启一个皇皇巨著的开端?
《马伯乐》,萧红 著,译林出版社 2023年4月。
戴锦华:我自己也是较晚才读到《马伯乐》。起初进入时有些读不下去,不是因为写得不好,而是从中我完全没有看到我期待的萧红。萧红遗言说:“留的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去写了。”我自己一直将这半部“红楼”理解为中国文人一个共同的遗憾或预言,它不是一个确指。这句话意味着她的写作就此中断了。我从没有从形而下的意义去思考这个表述,说实在的,《马伯乐》达不到半部“红楼”,但是在31岁的年纪写出这样的作品的萧红,她的生命是半部“红楼”,如果续写下去会是怎样?大概这是我们的想象力所无法抵达的。每次读到她的那句遗言,我都觉得其中有一种惆怅、留恋和不甘,还有一份旷达和对生命的彻悟。
格子:自比“留下半部‘红楼’”,是不是也说明某种程度上萧红对自己的文学地位还挺有自觉性的?
戴锦华:这就要回到萧红个人的生命。今天我想如果大家还保持一点起码的对文学评价的公正性,大概都会承认萧红比萧军写得好,端木蕻良就不拿来比了。可萧红生前一直在给他们誊抄稿子,洗衣做饭,认为自己没那么重要。所以萧红有没有这么张狂地把自己的创作比作半部“红楼”,我没有把握断定。
刚才我们说起撕扯,祖父的暖与父亲的冷相互映照,一个意味着挽留,一个意味着逃离,这只是她撕裂的一面。另外一面是,她生命中的勇敢与脆弱也在彼此撕裂。萧红的生命中有与生俱来的骄傲,但作为一个新女性,可能不仅是那个时代的新女性,比如说在我自己的成长经历当中,我们就是要终其一生去战胜那种怀疑,那种无名的自卑感,那种完全无法自我相信,自我确认的所谓的“本能”,这是撕扯萧红的另外一种力量。
我觉得她与生俱来的骄傲,也许会使她对自己有很高的期待。我仍然记得《萧红传》当中那个细节,她开始和端木一起生活后,当她再遇到朋友时,她伸出的那只手是软绵绵的,不再像当年那样强有力地跟朋友握一握手,相反她很女性化地伸出她的手。这种细节表现出她内心可能经验到的和她正在经验着的那些东西。我总是会说,这些经验大概只有女性先有其体验,对于整个社会,对于男性社会来说,就叫做“不为外人知,亦不足为外人道”。因为说起来都很琐细,都难以浮于言表,但是它真切地存在着。
4
萧红作品的左翼色彩:
赋予被剥夺了表达的人生命的尊严
格子:萧红书写了很多乡村女性。今天我们在讨论女性话题时,更多关注城市、甚至是中产女性,回看萧红书写的乡村女性时,戴老师有哪些感受?这个话题在今天是否未得到足够的重视,还是说已经同化为中产女性的问题?
戴锦华:萧红笔下的乡村女性非常鲜活饱满,但萧红并不是要把她们书写为女性,而是使她们作为女性所背负我们的历史,被看见。这是我理解的萧红作品中的左翼色彩。
整体而言,我觉得左翼文学之于中国整体是特别重要的。它完成了一种反转,达成了一种建构,让我们看见那些最底层、最贫穷、没有语言能力、甚至被剥夺表达的人群,它赋予了她们某种生命的尊严,使得整个中国文学有一种向下看的认同。在世纪之交的今天,这是我们逐渐丧失的。此时,当我们再去特别讨论性别问题时,完全没有考虑性别问题是人类的一半问题。
今天,当我们再次把萧红作为伟大的女作家来讨论时,加不加“女”字都成立,这意味着我们能否反思自己,真正承受那些背负历史却无法言说的女性的存在,直视她们的生活,这帮助我们去不断打开和解放自我。

电影《新女性》(1935)剧照。
格子:我有一点意难平的地方,即便当年跟萧红走得非常近,甚至很提携她的,比如鲁迅先生,其实当年对她的评价都不如我们今天这么高。在今天看,我们会觉得有点惊讶。我不认为鲁迅先生有意打压她,也绝对不认为他不欣赏她,反而是非常欣赏。即便是这样,很长时间里,萧红并没有得到像今天这样的承认,您觉得原因是什么?
戴锦华:我分两层来回答。首先,这批东北流亡的青年能走上文坛,很大程度是因为鲁迅的存在,因为他的提携引荐。他对萧红的评价,我大概不会把它放在低评价的意义上,而是一个完全无间隔的师生情感的关系。鲁迅先生对青年作家的评价都是同样的直接,这不是他特别针对萧红。当时他们的关系也并不涉及评价,而是一位青年作家在创作,一位年长的作家在同她交流。
其次,这涉及对萧红作品的整体评价。萧红生在极端残酷的抗日战争年代,随后又是全民动员的战后重建。在那样的历史背景下,我觉得她很多的同代作家都被搁置,或者说被旁置了,我不认为萧红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从一开始,萧红就被写在文学史当中,只不过她总被放置在群体中,没有被单独凸显出来。当我们开始有些闲暇去反思回顾,她就在我们的视野中突出了。
当然,部分男性研究者确实下意识选择了一种俯瞰的视角。当他们面对一个女性的时候,居然可以做到如此挑剔。在萧红作品中,很多人会觉得她不过是一个女作家,一个身世坎坷或者绯闻缠身的女作家,一个31岁就夭折了的女作家,她能有多么重要啊?我觉得会有这样一些先入为主,使他们没有真正深入萧红的世界。
5
写萧红生命故事,
难点之一在于重新讲述我们的历史
格子:我们已经看到一些影视作品中塑造的萧红形象,最出名的可能就是《黄金时代》了。您目前看到的在银幕上的萧红形象,您觉得够丰富立体吗?
戴锦华:许鞍华导演是我非常好的朋友,我在电影院里看了两次《黄金时代》。在《黄金时代》之前还有一部《萧红》,导演是霍建起,那部作品有它的流畅,但是他们把萧红写薄了,把萧红写简单了。我并不是在责怪导演,写萧红太难,写萧红不可能不写她的生命故事,但是写她的生命故事又如何能够写出她作为一个20世纪伟大的中国作家的文学画卷?如何写出她留给我们的记忆贮藏器——我们借用萧红的作品去叩访那个时代,进入那样一片光荣的土地。
《黄金时代》我觉得非常有趣,电影一开始,汤唯对着镜头说,我叫萧红,我生于哪年,死于哪年,那个时候我已经有一点惊愕了。因为一开始主角就作为一个死者出场了。接下来电影通过每一个萧红生命中重要的人去讲述她,去展现她。但是我觉得萧红在影片中所在的地方是一种空洞,大家围着她、讲她,可是这些讲述并没有让萧红占据原本应该占据的中心位置,没有让萧红这样一个非常丰满的又非常传奇性的鲜活的生命,在银幕上鲜活地和我们相遇。
我接下来的观点不是出于和许鞍华导演的交情,许鞍华导演不在意我对于她有什么批评,但是我真的觉得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导演没做好的问题。今天的整个中国文化,我们如何重新去描述,重新去讲述20世纪中国的历史,重新去讲述这蜕变的一百年和此前的中国文明史之间的连接和断裂,我觉得对我们整个文化来说都是问题和挑战。这件事其实我们并没有真正地做出成就,我们开始做了,但是做得还不够好。这就导致讲述的内容是一种真空,一直只有这些语言或者叙述在回旋,一直不能到达我们想讲述的那段历史。
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黄金时代》不过是一个案例,它给了我们双重思考,一重思考是说我们作为今人,如何去重新叩访20世纪。另一重是我们作为后来者如何能够真正在那个平行的、拉扯的、撕裂的脉络当中去理解萧红。我觉得它表明了这样一个挑战的难度和高度。
格子:这部并不让人非常满意的电影,几乎成为了在影视形象作品中我们定义萧红的一部作品,以至于我们今天的活动标题都叫《她和她的黄金时代》。我觉得其实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一个遗憾,就是我们拥有太多的选择之后,我们反倒很少愿意去回到原来的文本。

电影《黄金时代》(2014)剧照。
格子:今天能抓住戴老师不容易,我想问一些开放的问题。戴老师您认为萧红和张爱玲谁更好?
戴锦华:当年我写《浮出历史地表》的时候,我会迟疑,现在我不会迟疑,萧红更好。
《浮出历史地表》每一次再版都会有一个后记。我在一次后记当中说,当年我以为我发现了张爱玲,是因为当时在中国没有任何人谈论她,当时在中国的文化市场上没有任何人可以读到她,我们没有任何张爱玲的出版,而且当时她完全从文学史当中被抹掉了。我在电影学院图书馆的一堆旧书里(是一位老先生去世以后家人捐的)读到一些40年代的女作家选本,读到了《倾城之恋》,完全地被震惊,极度的惊艳。写《浮出历史地表》时我完全没有参考资料,如果你们读《浮出历史地表》的话,会发现关于张爱玲的生平我全说错了,但是再版这么多次我都没有改,我就把历史的错误留在那,我一点都不惭愧,就是因为没有任何参考的材料,我开始通过文本去理解张爱玲。就文本的理解来说,到今天为止,我不认为我的理解有什么误差,夸张一点说,我甚至不觉得有什么遗憾,以至于我没有再写张爱玲,因为我没有什么补充的话要说。
当时我以为我发现了张爱玲,但是到《浮出历史地表》出版的时候,张爱玲热已经开始了,回观这段历史,我觉得我无功可居,也没有什么罪责可负,我觉得在张爱玲的流行当中,我只不过是又一次流俗了而已。我跟着这个时代做了,又跟着时代流了一次俗,因为我认为张爱玲代表了她那个时代文学书写的最高程度。也正是她所在的那个时代,使得那样一种角度,那样一种书写,那样一群人能够跃然纸上。
我大概还是会用茅盾先生谈五四时代一位女作家的说法来讲,我觉得张爱玲书写了一个未死方生的人群,他们从旧时代走来,进入到这个新的时代,他们是旧时代的移民,又是新时代某一种意义的重新开启者。而今天我们很容易看到这些人,他们其实属于一个特殊的空间,比如上海和香港,他们属于一个特殊的阶层,不能叫贵族,是类似旧式乡绅这样一个阶层,同时又染指了新的资本结构。这是今天张爱玲被广泛地阅读、被不断地高度评价的一个原因。因为当她重新返回到中国文学视野的时候,刚好中国社会、中国城市开始形成这样一个群落,这个群落有文学趣味、会做文学阅读,同时家里有几个剩米闲钱,因为教养和教育,因为自我思索开始有了性别意识,所以张爱玲是一个多重历史时刻所造就的一位奇特的女作家。
而在这个意义上,我仍然要说,今天我反观我会觉得萧红更广阔、更深邃。或者我说一个不准确的描述,我觉得张爱玲留给我们的是一种趣味,一种情调,一种文学的美。而除了是一种文学的美之外,萧红留给我们的同时也是一个文学的世界,是一段历史,一段历史的书写。所以,我会说如果一定让我选的话我选萧红。
6
“可写的东北”与“含泪的微笑”
格子:不知道您会不会去关注东北文艺复兴这个话题,您有没有看到复兴萧红这一脉络的东北文艺复兴作品,或者说有这样气质的作家?
戴锦华:如果你指的是现在文坛所命名的东北文艺复兴,我必须说没有,我没看到能够纵深到萧红这样的深度或者这样的一个历史绵延线索的作品。东北文艺复兴这个说法出现以后,我自己没有再参加过类似的讨论。
比文学的东北文艺复兴开始得要早得多的是电影,是《钢的琴》,是刁亦男的《白日焰火》,是《暴雪将至》。那时候我提出的观点叫“可写的东北”,这里指的就是东北老工业基地。

《白日焰火》剧照。
东北老工业基地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经历了国营大中型企业转轨带来的失业冲击波,他们经历了从共和国长子、工人老大哥,到流离失所的、下岗的、漂移的、无助的人群的变化。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兴起和衰落,我觉得经由这些电影,第一次对中国社会所发生的这一切形成了一种讲述,它给了我们一种书写的可能。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提出了“可写的东北”。其实有很多作家包括很重要的中国作家,他们出了新作品来征求我意见的时候,我有点不礼貌,我就说我不喜欢。我觉得他没有感动我,他没有说服我,他没有吸引我。有一种常见的作家辩护词——我每一个人物都有原型,我每一个事件都有真实的依据,但是读起来就这么不吸引人,这样的没有说服力,甚至我们觉得是假的。我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说,这批电影提供了一种书写我们现实的可能,为什么真事儿写出来不令人信服,因为我们没有找到一种去书写它,去阐释它,去再现它,去和读者共享的路径。
我觉得是电影开启了这样一个可写的东北,后来它延伸为一批中青年的东北作家形成的东北作家群,他们又用文学的方式来创造,我觉得他们也可能是从电影中受到了启示,来创造这样一种我们表面上看是一个可写的东北。其实也是一个可写的当下。
我们很久没有遇到《漫长的季节》这样一个现象级的电视剧了。我觉得有两点很好玩,一个是作为一部东北题材电视剧,它是在云南拍的,另一点,我们所有的人在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都有自己的感同身受。我们不是在看一个远处的东北,我觉得这也是当年和今天我们阅读这一类作品的时候受到的触动。我们是在望向一个黑土地,望向一个遥远的时段,我们之所以读进去了,是因为它让今天的我们有了新的触动。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说,东北不是一个抽象的地理概念,它是一个非常具体的指向,一个非常具体地在我们今天的文化格局当中的位置,而这个位置大概还不能让我们很自然地延伸到昔日的东北作家群。因为昔日的东北作家群生存在那样一个背井离乡、那样的一个被迫逃亡,那样一个充斥战乱、挣扎、转折,充满了爱国激情,又不断地被打击而溃败的历史时刻。我想那段历史怎么连接上我们今天的现实,恐怕需要另外的历史契机,而不是一个新的东北作家群和昔日的东北作家群的连接。

《漫长的季节》剧照。
读者提问:戴老师您好,您在《浮出历史地表》这本书里面评价萧红的《呼兰河传》,您写道萧红的作品内含坦然平静和巨大的悲悯。现在的一些东北相关的文艺作品,比如说您提到电影《钢的琴》,在观看的过程中,我也同样地感受到了。还有您提到《呼兰河传》,萧红是在以一种“含泪的微笑”态度去回忆她的小城,在现在的与东北相关的作品之中,我也同样感受到了这种类似的内核,所以您觉得虽然说现在的东北的文学书写,可能没有和萧红写作那个时期有着历史上的连接,但是否他们的文化内核有着相近的脉络呢,这是我的问题,谢谢戴老师,我本身也是东北的,家乡是东北。
戴锦华:东北的孩子。我必须先说明《浮出历史地表》是我和孟悦的合著,我和我的女性同伴、朋友当年一起合作这个作品,当时她正在读文学史的硕士,所以专业的部分,文学史的框架都是由她提供的,我更多地贡献比较感受性的、阅读的、文本细读的这类东西,刚才每一次提问我都想补充这个,否则我就是贪天之功以为己有,这很无耻。孟悦很早就旅居海外了,所以我在后记当中也写,我说我就全权继承了做这本书的发言人的资格。
回到你刚才的问题,你说的时候我才意识到《钢的琴》导演张猛,他当时描述自己的作品就是哀而不伤,含泪在笑。但是我自己大概不会这么描述,我觉得你提供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理解脉络。这个东西也许可称之为东北文化特性,或者东北性格、东北品格,某种意义上说,我觉得它真的存在。
我虽然不是东北人,但我也是能够辨认出这样的一种东北的底蕴或者一种东北的韵味,但是我自己就不大倾向于用这种地域文化视角来研究,因为我觉得我们用地域文化特征来研究,我们会把它窄化。刚才我说我们现在能够在云南拍部电视剧来讲东北,而我们全中国的人,其实是在这个东北故事里认出了自己,或者某种意义上,我们认出了一种认识现实的模板,这才是我更倾向于采纳的方法。
我觉得如果从地域文化角度入手,一个是我们把作品变窄了,一个是我们把东北变窄了,我们到底说的是萧红的东北还是萧军的东北,还是张猛的东北,双雪涛的东北?他们的想象性不足以真正地替代东北的个性和丰富性。
我曾读到维也纳爱乐乐团的第一小提琴手,他原来是在东北接受的音乐教育,从上海到东北接受的音乐教育,我当时非常地震动,我想这个东北不是一个东北,但他们共同构成了东北。所以他们一定不只有一种情感基调,不只有一种地域文化的底蕴,而我觉得你说的这种悲悯之感,更可能出自于20世纪的文化传统。我觉得20世纪文化传统给底层人赋予了尊严,给底层人赋予了某一种可能是知识分子想象的道德高度。这样我们书写他们生活的时候,才能够用一种悲悯的姿态,而不是嘲弄的,不是鄙视的,不是俯瞰的,它更多的是一种平视的,一种你即是我,我即是你的书写方法,这真的是萧红作品当中特别迷人的,很多作家书写底层人的生活、劳动妇女的生活,我觉得多多少少都带有一点外在的、旁观的、不自觉的优越。而在萧红的作品当中,我没有感到这种东西,我觉得这个可能更多的是20世纪的宝贵的历史遗产,而不仅是东北文化所赋予的。
张猛在他关于《钢的琴》的描述当中,非常明确地就是表达了这样的一个仰望,而不是俯瞰。他说这是一次致敬,而不是对一个悲惨遭遇的同情和怜悯,所以你特别准确地用了悲悯,因为这种悲悯是推己及人的,是共情的。所以我觉得你提示了一个很重要的理解的点,但是我建议我们可能要用一个更大的方式去理解萧红,去理解可写的东北。谢谢你的提问。
整理/申璐 吕婉婷
编辑/刘亚光
校对/付春愔








发表评论 评论 (3 个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