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对红楼梦叙述风格和语言特色的直觉以及反复的品味(当然也有一些证据),笔者感觉红楼梦中有两个半回大不似出自曹雪芹本人的手笔,而疑为脂砚斋所撰。

戴敦邦绘《享福人福深还祷福》
这两个半回即第29回“享福人福深还祷福,多情女情重愈斟情”的下半回,第30回“宝钗借扇机带双敲,椿龄画蔷痴及局外”的上半回。对应回目对故事情节的提示,即第29回“多情女情重愈斟情”的故事,第30回“宝钗借扇机带双敲”的故事为脂砚斋所撰。
这两回中的上下各两个半回,其分野十分明确,第29回大约从“且说宝玉因见黛玉病了,心里放不下”一直到此回结束应为脂砚斋所撰,第30回则是从开头一直到“欲待要说两句,又怕黛玉多心,说不得忍气,无精打采,一直出来”为止是。
当然,可能曹雪芹在统稿时,从中进行了一些衔接过渡性质的处理,因此可能分界没有这样绝对。下面,笔者首先按文本顺序对文本进行一些分析,然后再从文本之外点出一点证据,最后从中分析推论得出一些结论。
一、第29回相关文本分析
第29回的上半回和第30回的下半回,可以很明显地看出,由曹雪芹自己创作的这两个半回,是典型的曹雪芹的文风,即一切在仿佛生活本身的流动中,写出人物各自的特性,同时展现出生活的丰富和色泽。
譬如,在第29回的前半回中,写贾府一众人到清虚观打醮,其中贾府的排场、王熙凤的凶狠(打小道士一节),王熙凤的善于玩笑和言谈(和张道士开玩笑),贾珍对贾蓉的不着调的做父亲严厉,以及张道士的善于应酬以及宝玉小心地收藏起金麒麟以及黛玉的轻微的嘲弄等等,都无不如此,非常好看。
而在第30回的下半回中,则是红楼梦中非常精彩有名的两个故事,一个是宝玉到王夫人处去,王夫人正在午休,宝玉和金钏儿在无意中导出了一段动人而悲惨的故事,一个是宝玉看见龄官在地上画“蔷”而引出的故事,这两个故事在小说中既意义重大,同时又是不经意自然引来,都非常精彩。

刘旦宅绘金钏
但是,同样是在这两回中,第29回的下半回和第30回的上半回却有许多不自然不合理处,其文字和叙事方法也有许多与曹雪芹的文风和叙事方法不大相合,如果是曹雪芹本人写来,绝不会在同一回中显出这样大的差异。下面我们还是看具体的实例:
第29回的下半回,开始即是宝玉怪张道士给他说亲的一个过渡性段落,小说此处是这样过渡的:
贾母因昨日见张道士提起宝玉说亲的事来,谁知宝玉一日心中不自在,回家来生气,嗔着张道士与他说了亲,口口声声说“从今以后,再不见张道士了”,别人也并不知为什么原故。二则黛玉昨日回家,又中了暑。因此二事,贾母便执意不去了。凤姐见不去,自己带了人去,也不在话下。
且说宝玉因见黛玉病了,心里放不下,饭也懒怠吃,不时来问,只怕他有个好歹。黛玉因说道:“你只管听你的戏去罢,在家里做什么?”宝玉因昨日张道士提亲之事,心中大不受用,今听见黛玉如此说,心里因想道:“别人不知道我的心还可恕,连她也奚落起我来。……”
笔者以为,这段文字的出现不大合理,因为在前面,即在第29回的前半回中,固然写到了张道士以不十分正式的口吻说到给宝玉说亲,但无论是贾母还是宝玉抑或是黛玉,都没有半点不高兴,而且揆诸情理,也绝不会不高兴。

电视剧《红楼梦》张道士剧照
而且在接下来的情节上,即张道士拿宝玉的“玉”给别的寺庙来的道士们看稀奇,以及别的道士们纷纷把自己随身佩戴的宝贝拿出来送给宝玉,宝玉又提出将这些宝贝施舍给穷人等等,也显示出宝玉绝没有半点不高兴,而是很高兴。
如果真要写有些不高兴,也应该是写黛玉可能有点不高兴,而且黛玉不高兴,也不应该是因为张道士说亲而不高兴,因为张道士即没有正式说,且贾母又已经回绝,黛玉应该高兴才对;黛玉如果要稍有点不高兴,也应当是为宝玉私藏金麒麟而有点不高兴(黛玉当时只是表示了轻微的嘲弄,并没有真生气。这才是合乎情理的)。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过渡性情节呢?笔者以为,脂砚斋批书之余一时技痒,也想试试自己笔力写几页小说,曹雪芹也同意让他放手写几页小说,于是他接手便故意制造矛盾冲突,以便于他开展后续的情节。
第29回下半,其实情节十分单一(一心专在宝黛冲突的情节上,而脱离了鲜活的生活场景和生活流,而这恰是红楼梦最重要的叙事特色),除了上面所述的一个过渡,余下的就是制造了宝玉黛玉的一次没有来由的冲突。

戴敦邦绘《痴情女情重愈斟情》
这一冲突的“大戏”,如果孤立的看,似乎也过得去,矛盾冲突很激烈,大段的心理描写似乎也较为合乎宝玉黛玉此一阶段的爱情心理,但是稍一细较,就会发现其中有许多不合理不妥当处:
第一,前面我们说了,宝玉黛玉因为张道士说亲而不高兴这一前提是不存在的,因此,整个下半回的这一冲突的“大戏”的建立就没有依据。
第二,正因为没有依据,或即使有一点依据,里面的冲突也显得不自然,显得是故意的为了矛盾冲突而制造矛盾冲突。譬如里面宝玉砸玉的情节就显得过头:
那宝玉又听见他说“好姻缘”三个字,越发逆了己意。心里干噎,口里说不出来,便赌气向颈上摘下通灵玉来,咬咬牙,狠命往地下一摔,道:“什么劳什子!我砸了你,就完了事了!”偏生那玉坚硬非常,摔了一下,竟文风不动。宝玉见不破,便回身找东西来砸。黛玉见他如此,早已哭起来,说道:“何苦来,你砸那哑吧东西?你砸他,不如来砸我!”
整个小说中,“砸玉”的情节一共两次,第一次就是第三回宝黛相见宝玉砸玉,此一次砸玉奠定了宝玉黛玉爱情的基调,也表现了宝玉的某种“呆”性,同时具有某种象征意味,是十分精彩的文字。但是此处的第二次砸玉,就显得不自然,过头。

刘旦宅绘宝黛情深
首先,我们退一步说,即便宝玉甚至黛玉因为张道士说亲的事有点不高兴,也远不到“砸玉”的份上。为什么,因为前面许多次黛玉经常为宝钗和她的金锁而吃醋,宝黛两人也经常为此冲突,宝玉也曾几次在黛玉面前赌咒发誓,宝玉也不曾砸玉,宝玉怎么可能为了一个张道士并不认真的说亲来砸玉呢?
第二,砸玉过程本身也显得过头,不自然,譬如,宝玉砸玉时气愤到“心里干噎,口里说不出来”,“狠命”地往地下摔玉,没摔坏,竟然找东西来“砸”。如此的极端举动,有些不合情理,在艺术上也显得过头。
第三,与宝玉的诸多举动反应过头不自然一样,里面对黛玉的反应的处理也是不自然、过头的。譬如里面描写黛玉:
黛玉一行哭着,一行听了这话,说到自己心坎儿上来,可见宝玉连袭人不如,越发伤心大哭起来。心里一急,方才吃的香薷饮,便承受不住,“哇”的一声,都吐出来了。紫鹃忙上来用绢子接住,登时一口一口的,把块绢子吐湿。雪雁忙上来捶揉。”
黛玉如此剧烈的反应,在前八十回中,在各种吃醋、争吵、使气的场合中就没有过(第57回,黛玉听袭人说宝玉“不中用了”有过很剧烈的反应,但这与因爱情的缘故生气不是一回事)即使在第26回“蜂腰桥设言传心事,潇湘馆春困发幽情”中,黛玉到宝玉处去,自以为宝玉不给她开门,黛玉的反应也只是“越想越觉伤感,便也不顾苍苔露冷,花径风寒,独立墙角边花阴之下,悲悲切切,呜咽起来。原来这黛玉秉绝代之姿容,具稀世之俊美,不期这一哭,把那附近的柳枝花朵上宿鸟栖鸦,一闻此声,俱忒楞楞飞起远避,不忍再听。”

电视剧《红楼梦》中林黛玉剧照
如此剧烈的反应,一直要到后四十回中,在第89回“人亡物在公子填词,蛇影杯弓颦卿绝粒”,第97回“林黛玉焚稿断痴情,薛宝钗出闺成大礼”中才出现。而这两次剧烈反应,一次是宝黛爱情的悲剧的一个前奏和预演,一次就是他们爱情的悲剧性的终结。
而在此处的第29回,怎么可能会因为一个什么张道士的一个半开玩笑式的说亲产生如此剧烈的反应呢?黛玉的剧烈反应,除了上引的呕吐的情节,还有一个“铰穗子”的情节也显得过头不合情理。
“铰”的情节在前面出现过,在第17回中,宝玉因为“题对额”得到了贾政的表扬,于是众清客和小厮一齐上来把宝玉随身佩戴的东西抢了个精光,回来黛玉见她送给宝玉的荷包也不见了,以为宝玉把她送给他的小信物儿也送给人了,黛玉于是:
生气回房,将前日宝玉嘱咐他没做完的香袋儿,拿起剪子来就铰。宝玉见他生气,便忙赶过来,早已剪破了。宝玉曾见过这香袋,虽未完工,却十分精巧,无故剪了,却也可气。因忙把衣领解了,从里面衣襟上将所系荷包解下来了,递与黛玉道:“你瞧瞧,这是什么东西?我何从把你的东西给人来着?”黛玉见他如此珍重,带在里面,可知是怕人拿去之意,因此自悔莽撞剪了香袋,低着头一言不发。

年画《宝玉和黛玉》
我们看,铰香袋的情节出现在此处是很真实自然的,因为那个荷包是黛玉的心意,是他们爱情的一个见证,一个信物,如果把这样值得珍视的东西也没心没肺送给人,那现在手头正给你做的香袋还有什么意思呢?所以赌气就铰了。
但是第29回处的“铰穗子”的情节却没有必然性。而且我以为,曹雪芹既然已经在第17回就写了一个“铰香袋”的情节,就不会又自我重复地在第29回写一个类似的“铰穗子”的情节,况且这里的“铰”的情节和前面相比,差了一大截,曹雪芹应该不会容忍自己重复自己,而且是往差的方向重复自己。
笔者以为,第29回下半回之所以出现这种不自然、描写过头的现象,就是因为脂砚斋为了湊小说,就像我们今天许多电视剧的编剧导演湊戏一样,常常靠刻意制造矛盾,制造冲突来编造情节,而往往不顾及人物的行动及人物性格是不是合情理。
此外我们还可以见出,脂砚斋一时技痒,也想来写几页小说试试时,实在是功夫不够(其实要帮曹雪芹续小说,没有谁的功夫够),他所编造的情节,其实很多是有意无意的模仿,譬如“砸玉”是模仿的,“铰穗子”是模仿的,甚至“呕吐”也是模仿的(黛玉呕吐的情节最早出现在第57回,因此我判断当脂砚斋技痒写这两个半回的小说时,他已经看到了后面的许多部分,由此我猜测曹雪芹并非一定按顺序写下来,或者脂砚斋是在曹雪芹修改补充的过程中写的那两个半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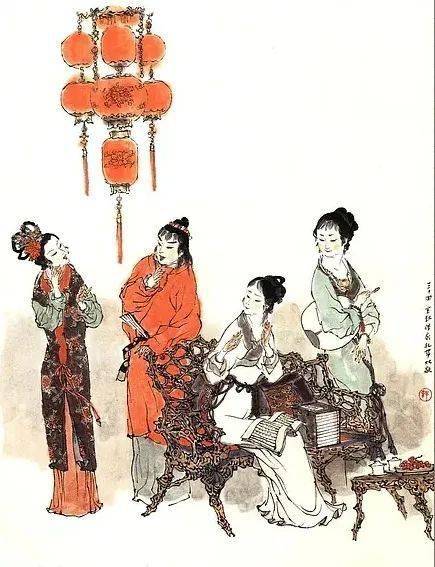
戴敦邦绘《宝叙借扇机带双敲》
第四,在叙述上,尤其是其中的大篇幅的心理描写上,采用了曹雪芹极少采用的外聚焦性的全知视角的心理分析和叙述方式。例如其中一段:
原来宝玉自幼生成来的有一种下流痴病,况从幼时和黛玉耳鬓厮磨,心情相对,如今稍知些事,又看了些邪书僻传,凡远亲近友之家所见的那些闺英闱秀,皆未有稍及黛玉者,所以早存一段心事,只不好说出来。故每每或喜或怒,变尽法子暗中试探。
那黛玉偏生也是个有些痴病的,也每用假情试探。因你也将真心真意瞒起来,我也将真心真意瞒起来,都只用假意试探,如此“两假相逢,终有一真”,其间琐琐碎碎,难保不有口角之事。
即如此刻,宝玉的心内想的是:“别人不知我的心还可恕, 难道你就不想我的心里眼里只有你?你不能为我解烦恼,反来拿这个话堵噎我,可见我心里时时刻刻白有你,你心里竟没我了。”
宝玉是这个意思,只口里说不出来。那黛玉心里想着:“你心里自然有我,虽有‘金玉相对’之说,你岂是重这邪说不重人的呢?我就时常提这‘金玉’,你只管了然无闻的,方见的是待我重,无毫发私心了。怎么我只一提‘金玉’的事,你就着急呢?可知你心里时时有这个‘金玉’的念头。我一提,你怕我多心,故意儿着急,安心哄我。”
那宝玉心中又想着:“我不管怎么样都好,只要你随意,我就立刻因你死了,也是情愿的。你知也罢,不知也罢,只由我的心,那才是你和我近,不和我远。”黛玉心里又想着:“你只管你就是了。你好,我自然好。你要把自己丢开,只管周旋我,是你不叫我近你,竟叫我远了。”
看官,你道两个人原是一个心,如此看来,却都是多生了枝叶,将那求近之心反弄成疏远之意了。

刘旦宅绘宝玉摔玉
我们且不管这段心理描写合理不合理,单从叙事手法来说,这种全知视角的纯然外聚焦式的心理分析方式,显得就是非曹雪芹式的。
曹公的心理描写,第一,没有这样大篇幅的外聚焦性的心理分析,第二,曹公的心理描写,一般都是采用内聚焦性的,从人物自身的特性和情景出发,从人物自己的内心里“吐”出来的,虽然在叙述上,它不能不借由一个叙述者来进行描写,但是在阅读感受上,我们却很少感受到这个叙述者的存在,仿佛就是人物自己在那里思想。作为一种比较,我们不妨引出第32回中的一段著名的心理描写:
原来黛玉知道史湘云在这里,宝玉一定又赶来,说麒麟的原故。因心下忖度着,近日宝玉弄来的外传野史,多半才子佳人,都因小巧玩物上撮合,或有鸳鸯,或有凤凰,或玉环金佩,或鲛帕鸾绦,皆由小物而遂终身之愿。今忽见宝玉也有麒麟,便恐借此生隙,同湘云也做出那些风流佳事来。因而悄悄走来,见机行事,以察二人之意。
不想刚走进来,正听见湘云说“经济”一事,宝玉又说“林妹妹不说这些混账话,要说这话,我也和他生分了”。
黛玉听了这话,不觉又喜又惊,又悲又叹。所喜者:果然自己眼力不错,素日认他是个知己,果然是个知己;所惊者:他在人前一片私心称扬于我,其亲热厚密,竟不避嫌疑;所叹者:你既为我的知己,自然我亦可为你的知己,既你我为知己,又何必有“金玉”之论呢?既有“金玉”之论,也该你我有之,又何必来一宝钗呢?所悲者:母亲早逝,虽有铭心刻骨之言,无人为我主张;况近日每觉神思恍惚,病已渐成,医者更云:“气弱血亏,恐致劳怯之症。”我虽为你的知己,但恐不能久待;你纵为我的知己,奈我薄命何!

电视剧《红楼梦》中林黛玉剧照
这大约是红楼梦中除了上引第29回的篇幅最长的一段心理描写了。
我们比较以上两段心理描写,可以看出它们在叙述上的巨大区别,第29回的心理描写,我们可以明显地感知到叙述者的存在,是叙述者从外面对人物的心理所进行的描写,甚至就是叙述者从外面对人物的一种心理分析,那些“心理”明显是外在的叙述者所给予的,与人物心理极其情景显示为“两张皮”。
而第32回中的心理描写,虽然在开头引出心理描写的几句中,我们也感知到一个叙述者的存在,但是一旦进入到心理描写本身,叙述者的存在就似乎已经隐去,其心理纯然是人物自己的心理,是此时此刻从特定情景中从人物自己的心里流出来的。
尤其是从“黛玉听了这话,不觉又喜又惊,又悲又叹”开始的心理描写,我们已经完全忘记了叙述者的存在,心理描写与此情此景与人物已经完全融为一体。
是不是仅仅此处的心理描写是如此呢?其实不是,举凡曹公的心理描写,都具有这样的自然自在与此情此景融为一体的品质,是一种内聚焦式的近于零度视角的心理描写。

刘旦宅绘黛玉
我们不妨再看第23回中的一段:
(黛玉)正欲回房,刚走到梨香院墙角外,只听见墙内笛韵悠扬,歌声婉转,黛玉便知是那十二个女孩子演习戏文。虽未留心去听,偶然两句吹到耳朵内,明明白白一字不落道:“原来是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
黛玉听了,倒也十分感慨缠绵,便止步侧耳细听。又唱道是:“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听了这两句,不觉点头自叹,心下自思:“原来戏上也有好文章,可惜世人只知看戏,未必能领略其中的趣味。”
想毕,又后悔不该胡想,耽误了听曲子。再听时,恰唱道:“只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黛玉听了这两句,不觉心动神摇。又听道“你在幽闺自怜”等句,越发如醉如痴,站立不住,便一蹲身坐在一块山子石上,细嚼“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八个字的滋味。
忽又想起前日见古人诗中,有“水流花谢两无情”之句;再词中又有“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之句;又兼方才所见《西厢记》中“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之句:都一时想起来,凑聚在一处。仔细忖度,不觉心痛神驰,眼中落泪。
此段心理描写,完全穿插在人物的行动和感觉中,与此情此景完全融为一体,虽然它实际也有一个叙述者的存在,但因为是内聚焦的,心里活动是完全从人物自己的心里流出来的,以致让人忘记了忽略了一个叙述者存在。

任率英绘《宝黛悟情》
第五,第29回下半回中的文字亦有许多不妥的地方。例如下面引出的几个例子:
且说宝玉见黛玉病了,心里放不下,饭也懒怠吃,不时来问,只怕她有个好歹。
笔者以为,这里的“只怕她有个好歹”一句不大妥当,黛玉生病在小说中间是常事,用黛玉自己的话来说,自打出生以来,吃的药比吃的饭还多。在小说中,黛玉生病时,宝玉从来都是劝慰她,也从来没有过什么“有个好歹”的想法。
再说,宝玉当时只有十五六岁年纪,何曾会如成年、老年人一样想到什么“有个好歹”。笔者以为,这样的“想法”实际就是写作的人,也就是脂砚斋不知不觉把自己的视角给了小说中的人物(而曹雪芹通常都是用人物自己的视角,也就是所谓限制视角来进行叙述的)所致。
原来宝玉自幼生成来的有一种下流痴病,况从幼时和黛玉耳鬓厮磨,心情相对。
此段文字,笔者以为有两处不妥,第一“下流痴病”的评价不大妥当。这段文字是以小说的叙述者、也就是作者的口吻说的,在小说中,曹雪芹自己虽然也会对自己给予贬低的评价,例如第三回中的《西江月》词二首即是。
但是那种贬低的评价大多都是一种反讽的写法,并不代表作者对自己真正的评价,而对宝玉此一种特性(喜欢女儿)表示贬低评价的,往往是别人的评价。而在小说第6回贾宝玉神游太虚幻景中,警幻仙姑所给予他的天下第一“意淫”之人评价,其实是对贾宝玉的一种嘉许。

秦惠浪绘《宝玉悟情图》
因此,这里的“下流痴病”的评价,实际来自于脂砚斋对书中人物贾宝玉的认识。能够佐证我们的这一结论的,恰好有一段来自脂批的评点可以与此相互印证:
宝玉品性高雅,其终日花围翠绕,用力维持其间,淫荡之至,而能使旁人不觉,被人不厌。贾蓉不分长幼微贱,纵意驰骋于中,恶习可恨。二人形景天渊而终归于邪,其滥一也。所谓五十步之间耳。持家有意于子弟者,揣此以照察之可也。(脂砚斋第63回回后批)
在脂砚斋的眼中,书中的男主人公贾宝玉实际是与小说中的轻薄纨绔子弟贾蓉是一路货色(而实际上,这种认识是与小说的主题表现大相径庭的),所以,在第29回的此处,他使用“下流痴病”来对宝玉进行描述,也就不足怪了。
此段文字的第二处不妥是“心情相对”这一用语,虽然这纯粹是一个用语问题,但笔者总感觉语言大师曹雪芹不会如此语言贫乏,“心情相对”不仅表述模糊,而且这用语有点“俗”,这与曹雪芹舌吐莲花,字字珠玑的功夫,似相去甚远。
那黛玉心里想着:“你心里自然有我,虽有‘金玉相对’之说,你岂是重这邪说不重人的呢?”
此段文字,亦有几点大可斟酌的地方:

于晓玲绘 《林黛玉与贾宝玉》
第一,这里将黛玉爱吃醋的心理完全写成了一种争宠的表现,而且写得过于直露。
其实前面许多情节中,黛玉尽管常常吃宝钗的醋,但是那是一种纯自然的心理反应,黛玉其实并没有往深处(即往婚姻方面想)想,相反,每次当宝玉当面向黛玉表白时,黛玉的反应都是愠怒的、含蓄的,如此方符合黛玉的年龄、身份和性格教养,如果如此直白地用“木石之盟”与“金玉之论”相争,将会有损黛玉高洁的形象,也会有损后来黛玉与宝钗的和好和相知。因此,我以为,持这种直露“相争”的感情,实只是脂砚斋作为读者的一个看法。
第二,也是两个用语方面的问题,一是“金玉相对”的用语,显示了脂砚斋语言的贫乏。
笔者以“金玉”为关键词搜索,里面有“金玉良缘”、“金玉之论”、“金玉姻缘”,第九十五回还有“拆散他们的‘金玉’”(原话是黛玉的一段心理活动:“ 果真‘金’‘玉’有缘,宝玉如何能把这玉丢了呢?或者因我之事,拆散他们的‘金玉’,也未可知”。)
第九十六回“瞒消息凤姐设奇谋,泄机关颦儿迷本性”中还有“‘金玉’的道理”(原话是贾母王夫人与薛姨妈商量让宝玉和宝钗成亲以“冲喜”时所说:“服里娶亲,当真使不得;况且宝玉病着,也不可叫他成亲:不过是冲冲喜。我们两家愿意,孩子们又有‘金玉’的道理”。)
我们看,在各种不同的语境中,曹雪芹对“金玉”会有不同的用法,都使用得恰到好处,但这个“金玉相对”不仅用语显得很平庸,与前面的各种用法显出很大的区别,而且我觉得“金玉相对”这个词组本身,就是一个模糊的表达,是一种不规范的口头语,什么叫“金玉相对”?“金玉相对”是成对,还是对立?
我想语言大师曹雪芹应该不会写出这样的语言,倒是前面脂砚斋有一个“心情相对”,或许这是脂砚斋喜欢用的词汇。

薛敏绘林黛玉
第二处不妥当的用语是“邪说”一词。黛玉的确是吃宝钗的醋,但那是少女的一种自然的心理反应,且此时宝玉与宝钗的关系并没有真正危及黛玉,宝钗自己也是一种无可无不可的态度,洁身自处的黛玉在相关的心理活动中怎么可能认为“金玉之论”是“邪说”呢?因此,这“邪说”的观念情感,实只是作为读者的脂砚斋的观点(脂砚斋大概是抑钗扬黛的),他不自觉地把自己的观念情感带进了小说中。
二、第三十回相关文本分析
第三十回前半回(从第30回开头一直到“无精打采,一直出来”为止)主要写了两件事,一是承接前面(第29回下半回)继续写宝玉黛玉继续为张道士说亲的事生气,第二是写宝玉嘲讽宝钗为“杨妃”。下面我们把这两件事分开说:
此半回写宝玉黛玉生气的部分孤立地看,要比脂砚斋刚开始写的第29回下半回要通达可读一些,但是它的一些根本性的缺陷仍然存在,这些缺陷都是由前面的情节设计而来的。
最主要的还是这三个方面,一是情节没有依据(此不赘述),第二是相关描写不自然,过头,例如里面写“黛玉两眼直瞪瞪的瞅了他半天,气的“嗳”了一声,说不出话来。见宝玉别的脸上紫涨,便咬着牙,用指头狠命的在他额上戳了一下子,“哼”了 一声,说道:“你这个——”
这些描写,都显得不自然,都有”为赋新诗强说愁“的毛病。此外还有一些描写亦是如此。
第三,就是有些描写很不合情理,且模仿的痕迹很重。例如下面“做和尚”的情节:

连环画《宝玉出走》
黛玉道:“我回家去。”宝玉笑道:“我跟了去。”黛玉道:“我死了呢?”宝玉道:“你死了,我做和尚。”黛玉一闻此言,登时把脸放下来,问道:“想是你要死了!胡说的是什么?你们家倒有几个亲姐姐亲妹妹呢!明儿都死了,你几个身子做和尚去呢?等我把这个话告诉别人评评理。”
这段文字中,其中有一些描写相当不合理。例如,当黛玉听宝玉说“你死了,我做和尚”后回答他说:“想是你要死了!胡说的是什么?你们家倒有几个亲姐姐亲妹妹呢!明儿都死了,你几个身子做和尚去呢?”黛玉的这段回答是很不合理的:
首先,所谓“做和尚”,本来是指自己所深爱的女人死了,万念俱灰,堪破红尘做和尚去,而不是指自己的姐妹死了做和尚去。黛玉怎么可能说“你们家倒有几个亲姐姐妹妹呢!明儿都死了,你几个身子做和尚去呢?”来回答宝玉呢?
第二,黛玉一直是以宝玉的心上人自许的,也知道宝玉爱她,持这种情感的她,怎么可能说“你们家倒有几个亲姐姐亲妹妹呢!”如果她这样说,就是将自己自居于宝玉的妹妹,而不是恋人的地位,而这在将爱情视为生命的黛玉的心中,是绝不可能出现的念头。
第三,黛玉在此种情形下,也绝不可能说出“你们家倒有几个亲姐姐亲妹妹呢!明儿都死了”这么不合情理也不吉利的话。因此,我判断,如此大的漏洞,就是脂砚斋在凭空极力制造冲突时,顾此失彼弄出来的。

陆小曼绘林黛玉
此外,在上引的情节中,“你们家倒有几个亲姐姐亲妹妹呢!明儿都死了,你几个身子做和尚去呢?”还有模仿的痕迹,而且我以为模仿的还不止一处,第一处模仿的是第18回:
(宝玉说)“该死,该死!眼前现成的句子竟想不到。姐姐真是‘一字师’了!从此只叫你师傅,再不叫姐姐了。”宝钗也悄悄的笑道:“还不快做上去,只姐姐妹妹的!谁是你姐姐?那上头穿黄袍的才是你姐姐呢。”
另一处大约是模仿第100回,其时探春远嫁,宝玉不由悲伤自己的姐妹死的死,远嫁的远嫁,于是宝钗质问宝玉(其时他们已结婚):
据你的心里,要这些姐妹都在家里陪到你老了,都不为终身的事吗?要说别人,或者还有别的想头。你自己的姐姐妹妹,不用说没有远嫁的;就是有,老爷作主,你有什么法儿?打量天下就是你一个人爱姐姐妹妹呢?要是都象你,就连我也不能陪着你了。大凡人念书原为的是明理,怎么你越念越糊涂了呢。这么说起来,我和袭姑娘各自一边儿去,让你把姐姐妹妹们都邀了来守着你。
我想,这就是第30回中那段话的部分由来,脂砚斋大概对这两处有关“姐姐”的描写记忆深刻,所以在第30回就模仿着写出那一段,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第18回和第100回中,有关“姐姐”的一番说词多么自然合理,但是第30回中,则显得生拉硬扯,很不合理。
其实,在第30回前半回的那半个故事中,还有一些也有模仿的痕迹,如黛玉的半截话“你这个——”、黛玉扔“绡帕”给宝玉擦眼泪,黛玉和宝钗、宝玉有关“负荆请罪”的一段冷嘲热讽也有较明显的模仿的痕迹。

陈政明绘宝黛读书图
另外,这段故事中王熙凤说的“乌眼鸡”、以及“黄莺抓住鹞子的脚,两个人都扣了环了”的笑话等也都是通过模仿写出来的。
大约点评过红楼梦的脂砚斋十分清楚,王熙凤只要一出场,大概就免不了说几个笑话,于是也如法炮制,让王熙凤说了两个笑话。
但我以为,王熙凤的这个“扣了环”的笑话并不恰当,第一,“扣了环了”的这个比喻过露,因为王熙风肯定知道王夫人和贾母都是恪守传统道德的人,不喜欢男女授受过于亲密。第二,王熙风肯定也知道王夫人和贾母真正中意的是宝钗,因此,尽管她也开过宝玉黛玉的玩笑(例如第25回王熙凤开的“喝茶”的玩笑),但不可能如此直露的开玩笑。
从这些模仿中我们可以看出,脂砚斋不愧是几次评点过红楼梦的,对红楼梦非常熟悉,但即便如此,他实在不可能脱离原作独立写出哪怕半页真正的小说,他所能做的,最多只能是有些神似的模仿。
下面我们再来讨论第30回前半回中的第二个故事情节,即宝玉讽刺宝钗是“杨妃”的情节。这个情节虽然短小,但是它在红楼梦中却非常有名,影响也非常深远。

电视剧《红楼梦》中薛宝钗剧照
为什么有名且影响深远呢?因为在整部红楼梦中,这大概是表现薛宝钗的“劣迹”最为昭彰的一次(第27回中滴翠亭宝钗“嫁祸”黛玉也算一次劣迹,但那次写得十分隐晦,最多也就是一种无意识行为),在相当的程度上满足了“抑钗扬黛”的人的情绪(脂砚斋大概属于这一派的人物)。但是笔者以为,这段情节却有相当多的不合理不妥当之处:
第一,这段情节在处理手法上有模仿重复第22回中湘云无意得罪黛玉(说黛玉像刚刚演出中的一个小戏子)的那个情节。
笔者以为,作为唯美主义者的曹雪芹,在写作上应该不会在此处又写一个类似的情节,第22回是湘云说黛玉像某个戏子,无意得罪了黛玉,而这里是宝玉说宝钗像“杨妃”,无意间得罪了宝钗。
第二,引出这个故事的转换处不是很自然,其相关部分是这样:
宝玉又笑道:“姐姐知道体谅我就好了。”又道:“姐姐怎么不听戏去?”宝钗道:“我怕热。听了两出,热的很,要走呢,客又不散;我少不得推身上不好,就躲了。”
宝玉听说,自己由不得脸上没意思,只得又搭讪笑道:“怪不得他们拿姐姐比杨妃,原也富胎些。”宝钗听说,登时红了脸,待要发作,又不好怎么样。
在上引的部分中,宝玉问宝钗为什么不去听戏(薛蟠的生日演戏),宝钗说怕热,于是推托身上不好,“就躲了”没去听戏。

《新评绣像全传红楼梦》贾宝玉绣像
就这么一段话,宝玉怎么会“由不得脸上没意思”呢?怎么会尴尬地“又搭讪笑道”呢?我想,这样没来由的话,只是脂砚斋为了引出那个“杨妃”的情节罢了,别的就顾不得了。
第三,宝钗的反应过于激烈,似乎也不大合情理。
宝玉把宝钗比作“杨妃”,宝钗是可能有些不高兴,毕竟在旧的传统语境中,杨贵妃是一个带有贬义的人物。但是,聪慧理性而节制的宝钗,怎么可能没事找事的又拉上“杨国忠”呢,说宝钗怕热,富胎,像“杨妃”,又关杨国忠什么事呢?
所以说,宝钗这样的不合理的反应,实在只是脂砚斋因为不喜欢宝钗,在此拉出一个“杨国忠”来暗示宝钗的虚伪。而这种对于宝钗的贬斥态度,实际有悖于曹雪芹对宝钗这个人物的定性。此外,宝钗突然对一个不知哪儿跑出来的丫头“靓儿”的厉声斥责,大不似宝钗日常的为人:
正说着,可巧小丫头靓儿因不见了扇子,和宝钗笑道:“必是宝姑娘藏了我的。好姑娘,赏我罢。”宝钗指着他厉声说道:“你要仔细!你见我和谁玩过!有和你素日嘻皮笑脸的那些姑娘们,你该问他们去!”说的靓儿跑了。

电视剧《红楼梦》中贾宝玉、薛宝钗剧照
如此声色俱厉,竟不似宝钗,而是凤辣子了。比较一下第20回宝钗喝止莺儿的一段:
贾环急了,伸手便抓起骰子来,就要拿钱,说是个四点。莺儿便说:“明明是个么!”宝钗见贾环急了,便瞅了莺儿一眼,说道:“越大越没规矩!难道爷们还赖你?还不放下钱来呢。”莺儿满心委屈,见姑娘说,不敢出声,只得放下钱来,口内嘟囔说: “一个做爷的,还赖我们这几个钱,连我也瞧不起!”
这才是宝钗的作为和声口,宝钗怎么可能会因为一个小丫头说的一个玩笑,如此地失态呢?我想,这也是脂砚斋因为要凑小说,故意制造冲突,另外,也是因为他对宝钗持贬斥态度,故在此把宝钗写得声色俱厉,以表示宝钗平日的稳重和平温柔敦厚都是假的。
第四,在宝玉无意得罪了宝钗之后,黛玉的得意之情也写得稍微过度,在此处之前,尽管黛玉多次吃宝钗的醋,使小性儿,但是都没有像此处表现得如此直露。我以为,这样写黛玉,就不仅是小性儿和吃醋的问题了,而是黛玉心胸狭窄,睚眦必报,将有损于黛玉的高洁形象。
三、一些外在的证据及推论
当笔者在阅读中凭其直觉嗅得这两个半回的非曹雪芹味道,并猜测这些文字多半是脂砚斋一时手痒而搞出来的时候,我就猜想,如果这是脂砚斋写的,他应该不会评点自己写的部分。

《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尽管笔者也曾经认真读过脂批,但也实在不记得他批过哪些,略过哪些,故我就又翻出脂批来查查,这一查非同小可,在本来批得很密集批得热火朝天的时候,居然有整整三回脂砚斋几乎完全没有批,而这三回恰好就是第29回、第30回,第31回。
第29回,没有夹批侧批眉批等,仅庚辰本有几句回前批,戚序本有几句回后批。第30回,也是基本只有回前和回后批,仅在甲辰本的“宝玉见他摔了帕子来,忙接住拭了泪。”后,有几句批语:“写尽宝、黛无限心曲,假使圣叹见之,正不知批出多少妙处。”第31回也仅有回前回后批。
然后从第32回开始,又恢复了前面那种比较密集的评点。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形呢?联系我对文本的感悟分析,我觉得这不是偶然的,这应该是脂砚斋一方面不好意思来自己评点自己写的东西,另一方面或他自己也觉得他写的那两个半回实在也没有什么好评点的,于是他就干脆不再去评他参与了的第29回,第30回。
那为什么连同他没有参与的第31回他也一并没有评点呢?这里面可能有两点原因,第一,如果他单单拈出第29回、第30回不批,这也太过显眼突兀,于是在第31回缓冲一下。第二个原因,就是第31回虽然脂砚斋没有参与,但是第31回却与前面他参与了的第29回和第30回紧密相关,因为在第30回的下半回和接着的第31回中,曹雪芹用比较明显的方法好几次照应了前面第29回下半回、第30上半回脂砚斋写的内容。

戴敦邦绘《 龄官划蔷痴及局外》
曹雪芹这么做,等于是正式地接受了脂砚斋写的两个半回,给它们发放了许可证。既然如此,第31回就和第29回、第30回有了别样的联系,成了某种共同体了,所以,脂砚斋连同第31回,也就一起略过不批了。
为了把这个问题的来龙去脉了解得更清楚,下面我们就来看看曹雪芹是怎样照应第29回、第30回的相关内容的,同时分析一下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曹雪芹对脂砚斋所写部分的照应在第30回的下半回紧接着就开始了。在第30回的下半回“椿龄画蔷痴及局外”的故事中,宝玉隔着花草看见一个女孩子拿着簪子在地上掘,她开始以为是某个丫头在学林妹妹葬花,于是打算喊话要那个丫头不要这样东施效颦,但仔细一看,却是他不认识的一个学戏的女孩。在此处曹雪芹开始对前面的内容进行照应:
宝玉把舌头一伸,将口掩住,自己想道:“幸而不曾造次,上两回皆因造次了,颦儿也生气,宝儿也多心,如今再得罪了他们,越发没意思了。一面想,一面又恨不认得这个是谁。”
笔者以为,至少这段文字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给前面做照应。宝玉在此想到的“前两回”的造次,一是指第22回当湘云直率地说那个小戏子“像林妹妹”时,宝玉给湘云使眼色,要她不要说,免得“多心”的林妹妹生气。

邮票《龄官画蔷》
宝玉一片好心给湘云使眼色,却被黛玉看见了,黛玉大概认为你给湘云使眼色,就是认为我是个小性儿,而且实际上你在内心里也是把我比作那个小戏子,故而后来黛玉大为生气。
另一次所谓“造次”就是指本回的上半回,宝玉说宝钗像“杨妃”。根据笔者的分析,这第二次的“造次”实际上是脂砚斋写出来的故事,现在曹雪芹把第30回第二次的“造次”特意与第22回的“造次”并列在一起并给予照应,就等于把脂砚斋写的部分正式纳入到了红楼梦的整体中,不啻于给脂砚斋写的部分发放了许可证。
但是如果我们严格分析的话,其实说第22回宝玉的举动是“造次”,是并不符合事实的,因为在这个事情中宝玉完全是一片好心,在动机和方式上都不能称为“造次”。而且在第22回中,宝玉的心里活动也是“细想自己原为怕她二人恼了,故在中间调停,不料自己反落了两处的数落。”
我以为曹雪芹在这里之所以把其称为“造次”,只是为了让它和第29回的真正的“造次”并列,以达到给第29回脂砚斋写的部分以照应的目的,其用心不可谓不良苦。曹雪芹除了着急忙忙地第30回本回就给予脂砚斋以照应,然后紧接着在第31回的开头又给予了一次照应,其文字是这样:

胡若思绘宝黛情深
这日正是端阳佳节,蒲艾簪门,虎符系臂。午间王夫人治了酒席,请薛家母女等过节。宝玉见宝钗淡淡的,也不和他说话,自知是昨日的原故。王夫人见宝玉没精打彩,也只当是昨日金钏儿之事,他没好意思的,越发不理他。
黛玉见宝玉懒懒的,只当是他因为得罪了宝钗的原故,心中不受用,形容也就懒懒的。凤姐昨日晚上王夫人就告诉了他宝玉金钏儿的事,知道王夫人不喜欢,自己如何敢说笑,也就随着王夫人的气色行事,更觉淡淡的。迎春姐妹见众人没意思,也都没意思了。因此,大家坐了一坐,就散了。
上面这段文字是一段过渡性的文字,这段以后接着的就是“撕扇子作千金一笑”的故事。其中说的“宝玉见宝钗淡淡的,也不和他说话,自知是昨日的原故”和“黛玉见宝玉懒懒的,只当是他因为得罪了宝钗的原故”都是指第30回上半回中“杨妃”那件事。
笔者以为,这段过渡文字的主要功用,也是为了给予脂砚斋写的部分以照应,以将它们与红楼梦的整体“弥合”起来。
两次照应还不够,同样在第31回,曹雪芹还对此做了第三次照应:

赵惠民制重工粉彩瓷板宝玉黛玉读西厢
宝玉道:“你何苦来替他招骂呢?饶这么着,还有人说闲话,还搁得住你来说这些个!”袭人笑道:“姑娘,你不知道我的心,除非一口气不来,死了,倒也罢了。”黛玉笑道:“你死了,别人不知怎么样,我先就哭死了。”宝玉笑道:“你死了,我做和尚去。”袭人道:“你老实些儿罢!何苦还混说。”
黛玉将两个指头一伸,抿着嘴儿笑道:“做了两个和尚了!我从今以后,都记着你做和尚的遭数儿。”宝玉听了,知道是点他前日的话,自己一笑,也就罢了。
这段文字,很明显也是在为脂砚斋在第30回上半回写的部分进行照应,里面不仅有黛玉的“做了两个和尚了”的人物语言,而且作者还特别用叙述语言“宝玉听了,知道是点他前日的话”来更清楚地说明。其目的也是为了将脂砚斋写的部分与红楼梦的整体弥合起来。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些结论,进行这样一些推论:
第一,脂砚斋手痒,想试一试自己的身手,撰写第29回下半回和第30回上半回,是经过曹雪芹的同意的。
第二,脂砚斋写了后,尽管不大如意,毛病很多,但或许曹雪芹碍于情面,同时也觉得亦无伤大雅,放置于书中并无大碍。所以,他将其保留了下来,只是精心地在第30回本回和第31回对此做了大量的照应,以达到至少在表面上将其弥合于小说的整体的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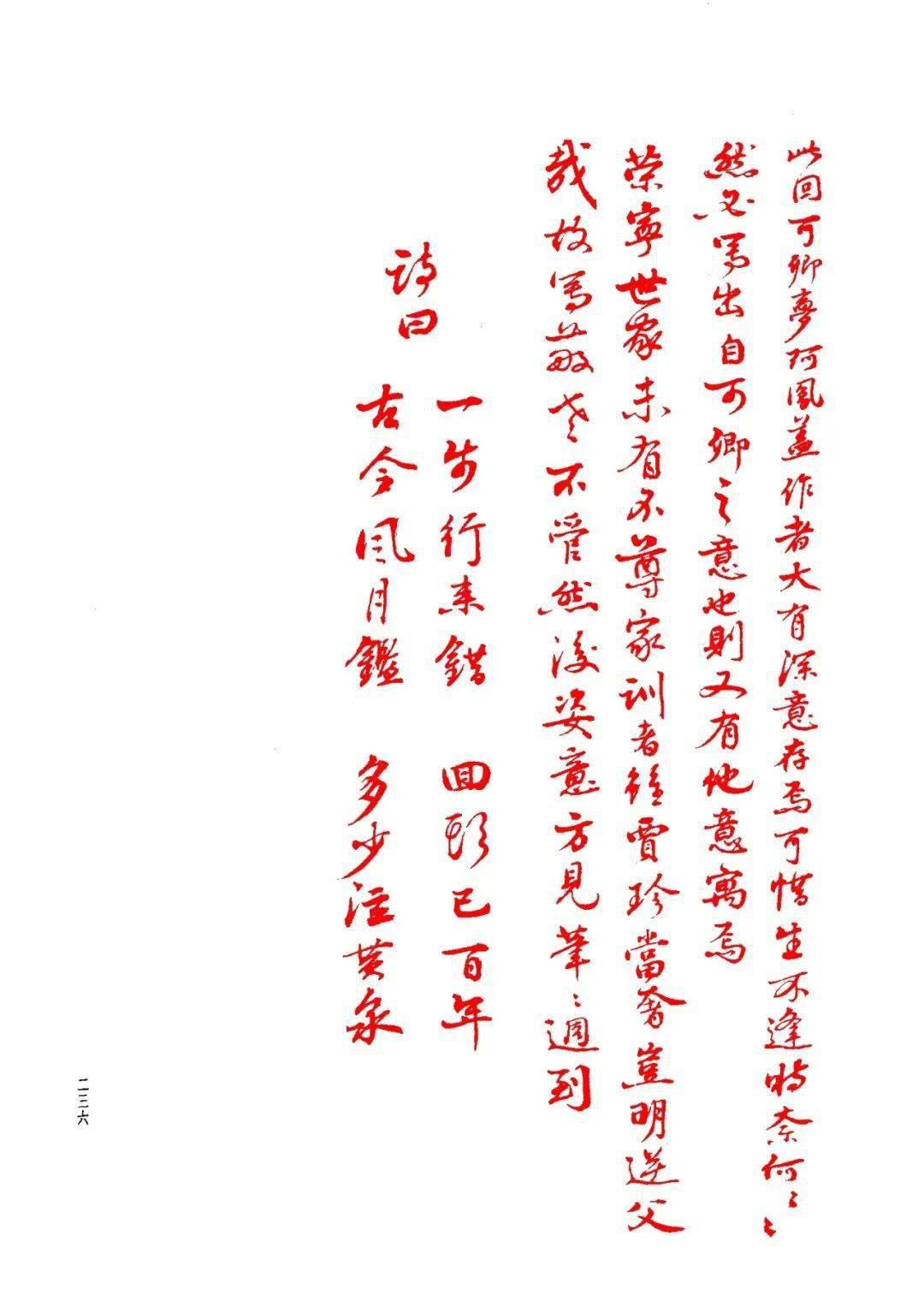
庚辰本脂批
第三,从此事件中,我们可以见出曹雪芹和脂砚斋两人的亲密关系,这种亲密关系乃至可以使曹雪芹让脂砚斋也来写一点试试。由此我们推论脂砚斋在红楼梦“缘起”中所批的“今而后惟愿造化主再出一芹一脂,是书何幸,余二人亦大快遂心于九泉矣”的批语绝非虚言。
第四,我们从中可以见出并推论,曹雪芹所写的尽管是“血泪家史”,其中无数都有真实的人物和事情作为依据,但是红楼梦绝不等同于自传,如果只是“自传”,脂砚斋也本是传中人,他亦能稍可作书,但实际上他并不能。第二,如果是重视于真实的自传,曹雪芹也不会放手让脂砚斋这样胡编。此外,我们由此代作事件揣其情景,可以见出红楼梦是一个充满创造的自由的写作过程,其中不乏虚构与创作,写作过程也充满自由和欢乐。
第五,尽管“一芹一脂”的关系非常亲密,但是,脂砚斋的作用基本只是“批书”,他们的所谓“共同创作”其实就是建立在一个写书,一个批书的合作方式中。脂砚斋,尽管与曹雪芹年龄大致相仿,有共同的受教育经历和生活经历(都从脂批中见出),水平也相当可以,但是,他绝不能代替曹雪芹来真正的创作小说,因为他都试过了,第29回下半回和第30回上半回就是他试的结果。
这两个半回,尽管他使出了浑身解数,前模后仿,又处处往宝黛的“大戏”上凑,制造矛盾,制造冲突,结果弄出的只是一些僵硬的(没有生活情景的自然流动及其人物性格自然呈现,这是曹氏小说的精髓)到处都是毛病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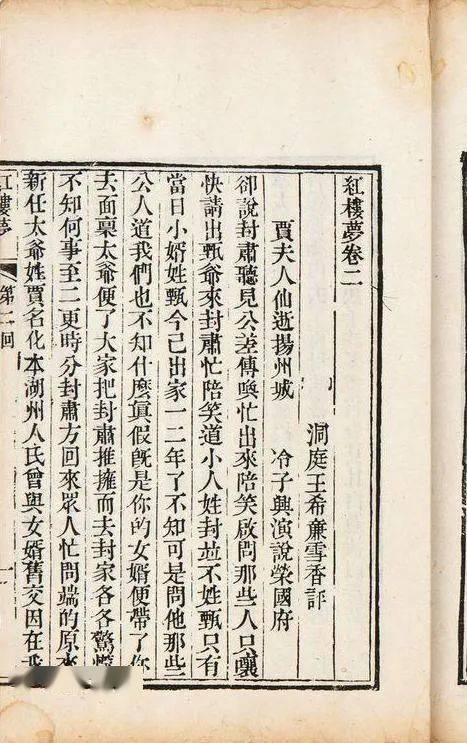
王希廉评本《红楼梦》
第六,由此我们可以知道,王希廉先生所说的帮别人续小说要比自己写小说难上千倍是千真万确的(见王希廉《增评补图“石头记”卷首“读法”》,俞平伯、林语堂也有类似论述),也由此我们可以推论(当然我们有百十种别的证据,不依赖于这一推论(见笔者《红楼梦后四十回真伪辨析》),所谓高鹗续写后四十回是一个天大的笑话,一个宇宙级的冤屈。
2021.11.5
谭德晶:解剖红楼梦这只大西瓜——析红楼梦的主题构成
谭德晶:论自《风月宝鉴》迁入部分的异质性
谭德晶:“一从二令三人木”新解
谭德晶:曹雪芹为曹颙遗腹子的两条铁证及其相关分析
谭德晶:《红楼梦》与《风月宝鉴》之关系再探
新书推介|谭德晶:《〈红楼梦〉后四十回真伪辨析》








发表评论 评论 (1 个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