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高星
我肯定地说,所有的写作者最一开始时都是由诗歌出发的,就像人的青春都是由怀春开始的,文学的渊源也是由诗歌开始的。
四十年前,张弛也是开始正经写诗。如他说是“四十年的积蓄”,那点激情,今天是否可以还能喷射。
后来,张弛主要写小说,后来写随笔、写剧本。作家不过如此,都是这样过来的。不过张弛有时会总是编排挤兑身边的诗人,夸奖写小说的狗子保持了从不写诗的状态。
其实,张弛断断续续一直写着诗,只是以前没有微信,大家不容易发现。张弛在自己准备印制的诗集后记中说:
后来所以少写至不写,完全是为了印证自己曾说过的一句狂话:好诗的数量是有限的,写一首就少一首。后来发现,不管写多写少,都很正常。一日为诗人,终身为诗人,这贼气不容易去掉。

写诗时候的张弛(黄燎原 摄)
张弛写于1981年9月的《圆明园》,是我目前读到的他最早的诗作:
第二次焚烧你的是一伙诗人
和你的农民大哥,自从那天
长着蓝眼睛的大兵
蹓蹓跶跶地出了村子
——问题不在于
他们只留下了笔和锄头
而是在于笔给了大哥
锄头却被诗人扛走了

从诗中可以明显发现,张弛在骨子里对诗人的敌视。这种敌视,哪怕就在自己写的诗作里。“笔给了农民大哥锄头却被诗人扛走了。”张弛的调皮和犯坏,不仅是乐于看诗人的笑话,而且是他一贯把玩的叙述的意外性。
张弛写于1984年的《作品》,可以是他写于1990年的小说《夜行动物馆》的前奏:
一反往日的矜持,你
良久注视着河水
河水的困劲儿
过去了,水面上浮出
大马哈鱼的脊背
(它老远便认出了你)
你顿时觉得自己的
脊背有些潮湿
看似意外的“潮湿”的通感,甚至是符合生物学的。
“语不惊人死不休”是诗歌写作的命根子。没有点本事,你还真写不了诗,这不是可以训练出来的。在这点上,阿坚、狗子彻头彻尾的写实法,肯定会在诗歌写作上有着阻碍的命门。张弛也在平平淡淡的叙述,在结局中的转化,充满魔幻,《阳历年》:
过去的日子频频回眸
眼药脱销 琵琶脱销
(波斯公主连夜潜逃)
围巾脱销肥皂脱销
狗拉着雪撬脱销
最冷的雪花
被裱在南方人的冰棍纸上

“最冷的雪花被裱在南方人的冰棍纸上”。地域、物理上的差异,让意想不到更加合理与矛盾,这是诗歌语言的秘密。但有的看似平淡,但在诗歌里就变味道,哪怕《饺子》:
乌云笼罩在饺子馆的上空
也笼罩在我的心头
中午吃了半斤饺子
(猪肉大葱馅的)
到现在还没消化
同样,下面这首《音乐会》,也是结尾的意外。而且,还有画面感:
小提琴锯断了 一节节木头
的音符,圆号的
喉咙 崩满铜锈
麦克风在电镀
歌声,指挥
晾干了最后
一件演出服
咕碌碌——
乐池里滚进
一个汽水瓶
所有的女孩,都
瞅了一眼
她们的男朋友

张弛的视觉肯定是另类的,诗人的眼睛是独到的,他的发现,总会有一条是精神层面的。《倒塌》一诗,让我想起埃舍尔的版画:“盖一栋倒塌的楼房”;“人往前走时会以为是在爬楼”;“他们直立时其实是在悬着”。荒诞的戏剧性,在张弛的文学整体写作中无处不在。这也是我观察张弛面对日常生活的颠三倒四,能够游刃有余,在所不辞的原因。
我要盖一栋倒塌的楼房
里面的人往前走时
会以为是在爬楼
他们直立时
其实是在悬着
在写于2009年的《黄没戏》中有这样一段:
一只仙鹤停在云中不动
一朵花不红照样开了
七个仙女只凑够了
四个,四天的旅行
一、一、七、四、四,诗作中的数字,总是有魔力的。在这点上诗人叶舟、西川也有过如此的经验。说到别的诗人,张弛很少在诗人里战队,他当然有自己的判断。他一贯是玩自己的,似乎是在语言的荒诞性上乐不可支。如同警句(金句)一般:“演员演完戏回家我却在剧场死去”(《悲剧》);“拉开电灯,墙壁上 起了一层鸡皮疙瘩”(《物理反应》);“一个孩子站在田里就像是一个成人被黄土埋了半截”。
张弛诗歌里的电影感也是如此熟来熟往,《三八妇女节》为他日后的电影进入进出打下伏笔:
今天是三八妇女节
窗外的云,显得
格外贤惠 我
想起母亲 和姐姐
(她 已经有了一个孩子)
我想到开火车的
一定是个女司机
她正在放慢速度
而这一天,也正在缓缓地从铁轨上挣脱出去
张弛在诗歌中,讲究言说的音乐性,这让我对张弛最近热衷音乐的现象,才不感觉突兀。《次旋律》有着摇滚风的旋律节奏,韵味十足:
一发炮弹在我的身边爆炸
把我兜里的巧克力溶化
几个路人躲到刺刀底下
显然是受到意外惊吓
花圃里面没有一朵鲜花
泼出去的水又收回去了
如花的闺女闹着离家
为的是跟大部队一起出发
依依依 呀呀呀
嘣嘣嘣 吧吧吧
这样的日子
这样的世道
张弛有的就直接命名歌词,1998年的《坦白(歌词)》:
一个人在默默地向我走来,
一朵花在阳光中无声盛开;
一把枪冷不丁抵住我的脑袋,
一个声音问我爱她不爱。
一阵风把天上的鸟儿吹歪,
一颗心由欢乐变得悲哀;
一句话始终没说出来,
这样的生活教我无法忍耐。
哦,坦白 让我坦白交待。

写于2020年8月的《歌词:鲁迅》,还有外一首,应是张弛最新的诗作:
他长着一头怒发
他穿着一件长袍
他是彷徨的旗手
他也食人间烟火
有人说他的脾气很大
那是他得了肺结核
有人说他的疑心太重
那是他看到的黑暗太多
他的目光很冷
他的血却很热
他有一些朋友
却也历尽孤独
副歌:
躲进小楼成一统
管它春夏与秋冬
装修队进楼(歌词),杂乱的声音,夹杂着杂乱的情绪:
自打疫情结束后
装修队就扛着家伙进了楼
他们一天到晚不停地凿
电钻一响更是把那大筋抽
精神不好的当场犯了病
(念白:比如邻居家的女儿)
男女老幼躲到山里头
原本盼来了好生活
想不到它比病毒更折磨
我钻钻钻
我凿凿凿
我拆了东墙补西墙
回过头又把那个东墙补
卧室变厨房呦
厨房变厕所
都是为了这幸福的节奏
(吵架声,做爱声,摔盆摔碗声,冲马桶声。
间歇性地伴随着凿击声,电钻声)
啊…………
叮叮叮叮叮叮叮
咚咚咚咚咚咚咚
都是为了这幸福的节奏
女声念白:
宝宝莫生气,你是妈**开心果
男声甲念白:
咦,兄弟你去哪儿,等一等,别把我落下
男声乙念白:
骄阳似火,你说我能去哪儿

张弛在诗里不仅有“副歌”、“念白”,还有“合唱”,他对效果总是有着强烈的预想。2007年的《脆骨》:
我冒着大雨去吃
落汤鸡的脆骨
却被告知
促销活动已经结束
这让我想起昨天夜里
做过的一个怪梦
两张单人床
在黑暗中并排空着
我居然当着大家哭出了声
以为就此找到了一生的幸福
合唱:
啊~
那些没了脆骨的鸡到哪里去了
那些没了脆骨的鸡到哪里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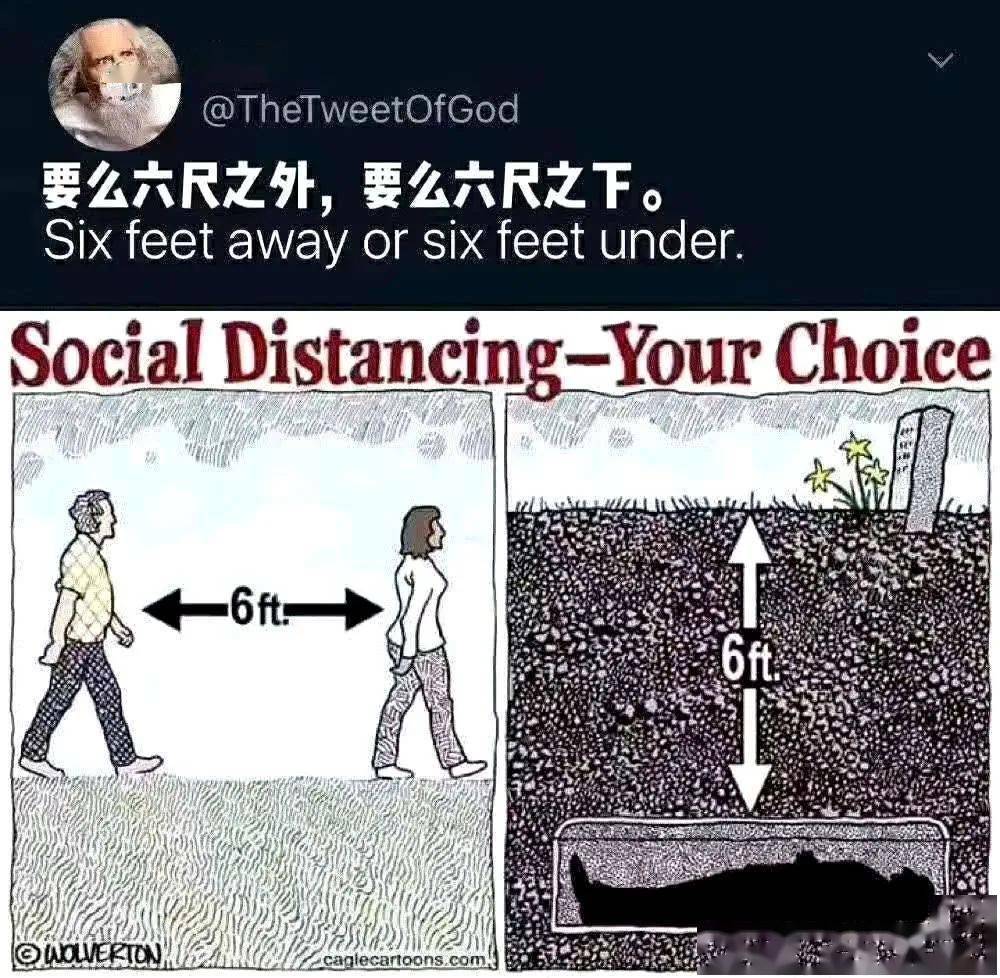
张弛在诗歌中的语言游戏,在他那里似乎已是雕虫小技。2014年的《呼和浩特》:
呼和浩特
是两个好朋友
今年夏天,他俩
决定去呼和浩特旅游
2017年的《府右街》:
一个交警
在府右街上
来回走
来走
回回
走来
(这几行竖着读)
当一个交警
在府右街上
来回走的时候
过往的出租
都不敢停

张弛打算将自己的诗集命名为《大事记》,其实,张弛是反大事的,如同拒绝宏大叙事,他在诗里极少见到爱情和美,他与这些诗歌本来应有的内容,背道而驰,2015年的《大事记》,应是他进入写诗新时期的代表作:
小区超市试营业
卖烟的服务员
原来是收破烂的(括弧:女)
狗不理厨师
躲在卫生间抽烟
被我撞见,他
迅速把烟掐灭
狗追喜鹊
两个诸侯国因
妇女采摘桑叶打仗
当然,这是在古代
国君们还要靠自己养鸡
犒劳前方的将士
还有一些大事
只能意会,不可言传
《幻觉》:
生活中有很多东西看似偶然
特别是在春天
从没跑过离城这么远
从没登过这么高的楼
从没见过这么多的云
从没有见过山被压得那么低
从来没有跟所爱的人
如此接近
特别是在凌晨
就在一周之前
出现了成团的柳絮
在四天之前
出现了绿荫
三天之前
降下了沙尘
两天之前
发现家里有了蚊子
——当时已是半夜
它跟困意一齐袭来
它飞翔的声音就如同幻觉
诗歌在张弛那里都不是什么大事,还有什么经得住考验?

后排右二为本文作者








发表评论 评论 (2 个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