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我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进修期间,喜欢乘灰狗巴士(Grey Hound)到各处旅行。去加州必到旧金山看望叶其璋和梁铨,其璋是伯克利加州大学的访问学者。伯克利大学城仍保留着上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的遗风。墙上可看到激进标语和列宁像,但街头过气的嬉皮士已再无昔日英姿。 那个年代能出国的中国艺术家大部分都在纽约落脚,纽约的机会多也容易谋生,许多画家在街头画像。到西海岸的中国艺术家不多,进入学校学习的就更少。当时其璋对旧金山湾区的艺术界已相当熟悉。他带我去参观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的工作室,还介绍我认识旧金山美术学院院长弗莱德·马丁①。马丁是艺坛元老,为人谦和热心。后来就是他与其璋一起倡建了旧金山美院师生到浙江美术学院(中国美院)学习的暑期班,这是中美之间艺术交流最早,也最成功的项目之一,一直延续了许多年。我也因在中国美院主持外事,一直和马丁联系不断,那些年我几乎每次去旧金山都会在他家借宿。现在我和马丁都担任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当代艺术顾问,见面时仍常回忆起当年与其璋一同在他的奥克兰书房中喝咖啡聊天的往事。 欣赏其璋近年的作品,立刻又想起我第一次从旧金山乘坐BART(旧金山湾区快速交通系统)跨海到伯克利,他在画室中让我看了一系列以树的枝干为对象的油画,很有新鲜感。观念绘画大约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才开始被介绍到中国,而其璋的画风这时已具有一定的观念因素,在当时大陆来的画家中并不多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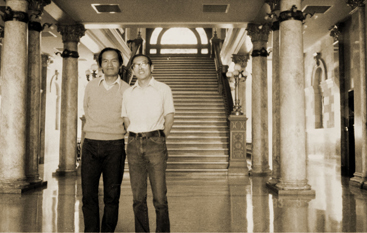
其璋年青时和许多同代画家一样,创作过不少“为政治服务”的主题画和宣传画。在这些人物作品中他展示了出色的绘画技巧。其实在风景画中他也很早就显露出敏锐的感觉。上世纪中国风景油画的发展主要受两方面的影响。首先是受到19世纪法国的印象派影响。早期留欧学生对这种风格已有直观深入的了解,并带回了外光写生的技法。但到了1950年代,由于意识形态的控制,印象主义和其他西方现代主义流派在中国都被列为禁区。记得在1957年初美术界曾有一场引人注目的辩论:许幸之等理论家认为“印象主义就是印象主义”,不必另加政治帽子;而美协领导江丰等却坚持认为印象主义不是现实主义,需要批判摒弃。在“左”倾观点的影响下,一些深得印象派要领的老艺术家(如颜文樑、周碧初等)都不被重用,而学生如略有模仿之意也会被视为越轨。后来“文革”中江青更明确地在《红旗》杂志发表文章,将“印象派”“抽象派”一起斥为腐朽、颓废、反动,应在打倒之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江丰后来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分子”,受尽迫害和折磨。“文革”结束后他恢复了在美术界的领导地位,所做的第一件好事就是允许风格比较多样的“迎春画展”在北京开幕,让多年见不到的风景画也在这次展览中露面,带来了新时代的开放信息。另一个重要的影响则是来自俄国的绘画。它们可以作为现实主义的传统艺术被接纳。在1955年于京、沪举办的俄罗斯与苏联油画雕塑展览, 是建国后第一次大规模地将国外原作展现在中国观众面前。列维坦②的《金秋》和库英治③的《乌克兰傍晚》都让倾心于风景画的艺术青年感到震撼。叶其璋吸收了这两方面学养,锻造了坚实的基础。记得上世纪60年代我们一起下乡写生采风,更多的是被派去参加各种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使是在政治风云的旋涡里,依然可以为田野水乡的秀丽明媚景色所陶醉。在我们住过的乡镇无不有一个个美丽的名字,诸如“枫桥”“夏湖”“花明泉”…… 令人神往不已。其璋的风景画就饱含了这种多年沉淀的对江湖山村的情谊,一直延续至今。后来在美国举办浙江美院师生作品展览时,我们有机会畅游蒙大拿的落基山岭和遥远的白鱼湖,在异乡的山水中也忍不住有作画的欲望。他一如既往地继续自己与大自然的交往。



经过国内外数十年的磨炼实践,他利用在海外的机会,探索当代艺术发展的轨迹,又根据自身的艺术素养和性格特点,继续思考艺术创作的实践方向。他对艺术有一份特殊的敏感和真诚,且甘于寂寞,能冷静地对待社会错综复杂的变化和世事更迭回转的起落。于是他选择了以大自然浩瀚的生态环境为伴,与树木、花草、山水、田野交融相亲,作无言对话。因此,当我看到他的风景画时最受触动的不是它的技巧渊源,而是艺术家对自然环境长年累月的接近和寻求。他极其尊重生态的自然存在,认为大自然的美是无可比拟的,只要将对象作适当取舍,不必大动干戈,任意破坏和改动它的有机结构。其璋的画多以树木为主体:有的拥簇层叠,有的亭亭玉立,有的叶片背光而显得晶莹剔透,有的迎着夕阳而尽染金黄嫣红。他画的几乎都是杂树灌木之类,并不是高贵稀罕的品种,也谈不上什么名山胜水的景色,只是寻常的丘壑半坡,或后园一角,有时还隐隐约约在枝缝间透出黑瓦白墙来。但正是这种看似不经意的一瞥,给这些画面带来一种亲切的乡土气息,也让我们看到艺术家在平凡中呼唤出深蕴美感的能力。他的画面平实沉稳,既不以突兀的取景标新立异,也不求鲜丽的色彩哗众取宠,而颇有一种信手拈来的感觉。但是越是寻常景色,越能考验艺术家的观察力与表现力。其璋这么多年的锤炼,才能使他的画面显得如此淡定,没有火气。但仔细看来,却在设色用笔上有自己的分量。他的画面上光影斑驳,让我们想起波纳尔④的影踪;而色彩的布局结构又颇得弗鲁贝尔⑤的启示。当然,他的借鉴并不限于此。在漫不经心而流畅自如的笔触之中,我们也可觉察到黄宾虹与波洛克⑥的表现手法。他在画面中简略了调子和明暗关系的转折,从平面色彩配置中探索空间,在作品中洋溢出那种自由激动,又理性剖析,呈现出无法预期的最后效果。
“绘画已死”的说法已喧嚷多年,但绘画依然充满活力。风景画也始终没有在我们的视野中消失过。美国艺评家D.彼得罗维奇⑦认为当代风景画所面临的任务既简单又沉重。由于风景画深得一般公众喜爱,也由于我们对环境的共同关怀日益增长, 为这一画种提供了巨大的机会。彼得罗维奇说:“ 一幅关于自然的绘画现在同样是关于我们自身行为的绘画。从这个角度来看,以前关于风景画的一般看法被分解到完全不同的美学、政治或其他不相干的领域中,背离了要探究我们与自然到底是什么关系的更宏大的期望。现在重建这一视野的企图不论是否完善或恒常都可有助于澄清这种状况。新的风景画要求有新的视野。我们长期以来习惯于看到我们从自然中要求什么,现在艺术家需要设法看到自然向我们要求什么。”
大自然对人类的要求其实很简单,就是不要去破坏、污染或滥用它,为后代保存一个生息有序的环境。同样,天然景色并不必以人为的美学规范或时尚品位来评判或修饰,它只需要艺术家的辨识和尊重。其璋多年来在风景画领域的努力也可以看作是他在大自然中的潜修,渐渐求得一种不浮不躁的平常心态。我一直认为“随心所欲”是艺术创作的出发点,也是它的最高境界。如果一位艺术家能忘情于自我,其实并不必在意所谓新旧进退之分。每当看到一张好的风景画时,我总会不由自主地默诵起陶渊明的名句: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2013年1月于温哥华
本文作者系学者、艺术家、独立策展人,《YISHU(典藏国际版)》总策划。
注:
①Fred Martin(1927— ),美国艺评家、艺术教育家。
②Isaak Levitan(1860—1900),俄国艺术家。
③Arkhip Kuindzhi(1842—1910),俄国艺术家。
④Pierre Bonnard(1867—1947),法国艺术家。
⑤Mikhail Vrubel(1856—1910),俄国艺术家。
⑥Jackson Pollock (1912—1956),美国艺术家。
⑦Dushko Petrovich,美国艺评家、艺术家。








发表评论 评论 (1 个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