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需要被记忆,时间需要被度量,而阅读无疑是将消逝的时间保存在记忆中的理想方式。阅读保证了我们以思考的维度来覆盖世界,通过阅读,我们将观察到的、看到的、经历到的事件融入自己的头脑,将流逝的时间烙上印记。它填充着我们的人生,也不断丰富着时光的意义。

2023新京报年度阅读推荐特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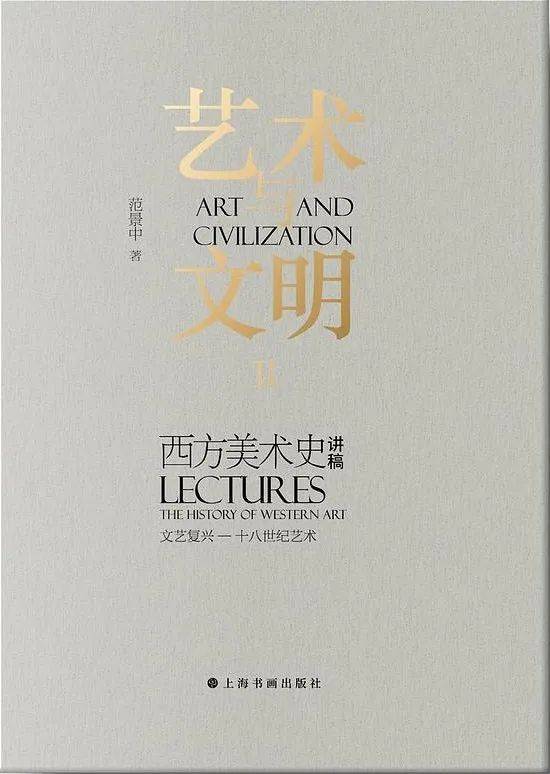
《艺术与文明II》
作者:范景中版本:上海书画出版社2023年8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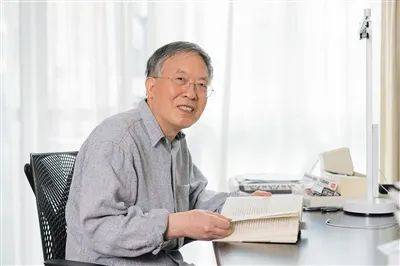
范景中,1951年11月生于天津。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范景中教授是当代中国艺术史研究的标杆人物。他最早将西方艺术史学者及其研究成果与方法介绍到中国;他首次将贡布里希《艺术的故事》翻译介绍到国内;他在20世纪80年代便倡议“美术史应是一门人文学科”,推动了美术史的独立发展及对其他领域之影响。
致敬词
近三十年来,风起云涌的“视觉文化”新美术史挑战着传统美术史的地位,以高昂的姿态抛弃价值判断,而代之以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性别学等的外围研究。范景中有意识地不使用专业圈内流行的各种崭新术语,围绕着风格的来由与根源展开论述。《艺术与文明》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西方艺术通史,它消化了许多最新的研究成果,呈现了诸多连接中外古今的思考。它是关于艺术的研究,更是关于艺术研究的研究。
我们致敬《艺术与文明》,致敬变动不居的人类文明中所孕育的灵感与创造力。我们也致敬它的作者范景中,以学贯中西的底蕴书写一部雄心勃勃的艺术史诗。
答谢词
很高兴《艺术与文明》成为新京报年度阅读推荐,我由衷地感谢新京报评选委员会对这本书的高度认可和肯定。
大凡著书的人,都能体会从存在的事物中去创造出新事物的感觉,很像艺术家学会了前人的图式去创造一幅崭新的画。可美术史家能从现存的事物中创造什么?这正是我写书时常常思考的问题。大体上,本书描述的艺术品,按照时间顺序,但却不像教科书一样面面俱到,而是想把我感兴趣的艺术作品和艺术问题,串成一部简单的通史,因此省略了不少很重要的作品。
对于文明,讲的就更少了,而且讲得非常含蓄。首先,我把美术史看成文明的代言人,因为艺术品让文明物质化,让文明可以触摸;又因为我没有高明的真知灼见对文明做深邃的表达,所以,就想仰仗艺术作品来呈现。就像斯宾塞在《教育论》中说的:“建筑、雕塑、绘画、音乐和诗歌,堪称文明生活的盛世。”也是这个意思。
此外,同样重要的,我也总是借助书籍、借助图像学的知识来提示。如此,是想突出我心中悬想的美术史的无用之用。一般来说,我把美术史看作一种熏习,一种烟云供养,一种指向文明的最重要、最不可或缺的矢量,用奥维德《黑海书简》中的话说就是:“潜心熏习博雅的艺术,让人心优雅,让野性消除。”这也是写作本书的主旨。
——范景中

颁奖嘉宾定宜庄(左一)、《艺术与文明》出版社代表(田松青,左二;黄坤峰,右一)在2023新京报年度阅读盛典现场。
这本书
摒弃流行的专业术语
新京报:你提及有意识地摒弃流行的专业术语,为何做出这样的选择?
范景中:我很理解年轻的美术史家对新概念和新词汇的迷恋,我年轻时也是这样。然而,如果没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基础,就难免会成为时尚术语的追星者,总是扑向套餐,埋没了自己点餐的能力。我知道这么说有点保守。然而,这也许能提醒年轻的美术史家,我们不用去理会权威的力量,不用去考虑群众的压力,不用去考虑时尚的诱惑。
我一直羡慕西方学者对于文艺复兴三杰的研究,那些论著可以垒成小型图书馆。对比而言,中国的艺术大师却很少有人关注,像王连起先生那样对《兰亭序》、赵孟頫作出精湛的研究,特别是从艺术⻆度作深入的研究,实在太少了。我们没有对艺术品本身作真正的研究,就迫不及待地跑到艺术品的外围打转,表面上是视觉文化,其实是美术史的解体。
新京报:有读者认为它不仅是关于艺术的研究,还是关于艺术研究的研究。你在书中对许多艺术史家的观点进行了论述,如何看待这样的反馈?
范景中:在前面讲到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实际上就是要弄懂学术史。由于我写作的初衷,把读者对象设定为美术史的本科生,所以我想以沃尔夫林的形式分析、潘诺夫斯基的图像学和贡布里希的“图式与修正”这些“美术史的普通知识”为主线进行讲解。
当然,除了这三者之外,也融入了当代的一些新的成果,有时也添入自己的一些评述。不过,写到最后,我发现这本书有些违背初衷,有时我也会跳进书中对作品进行解释,有些地方还有暗示性的评骘。尤其是我对沃尔夫林五对概念的“考镜源流”,几乎让这部书变成了一部个人色彩很强烈的书。
这个人
我是被语言打败的人
新京报:这部《艺术与文明》在你的作品中占据怎样的地位?有读者拿它与《艺术的故事》比较,这本书你也是译介者。
范景中:《艺术的故事》在2000年时,得到了影响20世纪百部著作之一的高度评价,我认为,那是名至实归。从写史的结构而言,它完美得令人掷书三叹。它用平实、浅近的语言讲述需要用一部《艺术与错觉》那样的杰作来论述的艺术发展史,更是让人赞美击节。所以《艺术与文明》在某种意义上是阅读《艺术的故事》的感想,就此而言,它也是一部读书笔记或札记。我从未想到会写这样一部书,这一点倒和《艺术的故事》一样,都是偶然的产物。
我写的书很少,上世纪80年代初读陈寅恪先生《柳如是别传》后就自我告诫:切勿写书。这也牵涉到我对一部书的珍贵特质的看法:一部书的珍贵总是让人对语言敬畏,同时又不时地流露出作者跟语言搏斗的痕迹,他要选好一个词、选好一种表达,都要费尽心机,以至于常常觉得,我们的语言远胜于我们自己。
毕竟,语言让我们成为人。后来,得了大病,接着眼睛又出了问题,不能再看英文的小字了,反而写了几本短小的书。不过,我写《中华竹韵》也是偶然。我真正想写的也许是从艺术的角度看书籍史,因为我常常想以一部书向书籍致敬向书籍感恩,可惜我已经没有精力写了,只发表了几篇文章。
新京报:写作这本书时遇到的最大障碍或者挑战是什么?
范景中:唐人刘知几要求写历史的人具备三个条件:才、学、识。后人又补充为德、才、学、识。用法国人⻉尔(Pierre Bayle ,1647—1706 )在《历史和批评辞典》(Dictionnaire Historique et Critique)中阐述的话说就是:“写历史是一个作家所能涉猎的最具难度的创作,它要求超常的判断,高贵、清晰、简洁的文⻛,出色的道德感,完全的正直诚实,能把大量宝贵的资料安排得井然有序的高超造诣;还有最重要的,要有抵御宗教狂热的力量,而这种狂热会扇动我们排斥真实的东西。”
以上条件,除了史德还自信未泯之外,其他条件也就那么一星半点儿。不过,我也幻想,如果再去国外从从容容地旅行一次,可能会比现在写得好上一些。但也不一定,也许得到更多的材料,反而更驾驭不住了。写长篇的书,要获得一个一以贯之的主线不容易,要把一个美妙的想法表达得栩栩有气韵不容易,要写得让自己过得去更不容易。只要写书,就处处是障碍,实际上,最大的障碍就是不论怎么写,自己都不满意。
我常说,我是被语言打败的人。我在《美术史的形状》前言中,曾向杨思梁和徐一维等人致敬,他们都有语言的天赋,我很羡慕很敬佩他们。我为自己过不了写作这一关,不得不在投老残年仍然学习而感到吃力。《艺术与文明》出了三册,每册我都不敢翻看;身为教师,不能不教学生,否则失责;但转为作者,就难免有愧于读者了。
这一年
艺术能救人于困厄
新京报:当下,了解艺术与艺术史能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
范景中:1986年我去敦煌,火车上遇到北京大学地理系的一些学生,我们聊起天来,我给他们提了一个建议,建议他们去敦煌,不只看地形地貌,更要多看艺术。因为艺术在人们成⻓的年月,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昂然而起,救人于困厄。我想,在疫情中,大概有不少人已经有了这种体验了。
新京报:这一年的生活与工作状态是怎样的?
范景中:我的生活很简单很单调,大都是在阅读中度过的。也许年龄大了,有句拉丁警句一直不敢忘记:视人生明日将逝,视学问永生无止。因此我也经常到学校,或是和学生探讨论文,或是倾听年轻老师讲他们的新知新获,这是我获得知识的重要来源。偶尔也会走进剧场沉浸在古典音乐当中。
我经常想起德国大数学家希尔伯特,他过了70岁,经常请一位年轻学者给他讲学术的进展。能在修途促景中还源源不绝地获得新知识的滋养,促动心灵中未僵硬的惊奇感,还有什么比这更美好的?
采写/张婷
编辑/荷花
校对/薛京宁








发表评论 评论 (1 个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