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天的评论界,评论家与作家之间似已形成了某种固定的“对位”关系,如重量级对重量级,这使得有的评论家似比作家本人更急切地期待并乐于在这种时候应景出场,这实在是很要不得的事情。
今天文学批评的整体生态不尽如人意,已成社会共识。在必须重建批评伦理这个问题上,专家的意见更从没有像今天这么一致。但之所以它仍一再成为人们聚焦的话题,是与批评者普遍陷入知行背离的窘境有关的。
这样的窘境在今次贾平凹新作《山本》的评论上再次上演。
由于其写作的精神资源许多时候与当下的商州、西京和秦岭是脱开的,他对乡村的迷恋因此仅表现为一种不易为人认同的骸骨迷恋。

贾平凹无疑是新时期以来具有重要影响的作家,对于他的成就,批评家们说了许多,个人也很钦佩。要说有所不同,是自己更喜欢他的散文,对他的小说则稍有保留,为其越到后来越堕入固定的程式。总是在缺乏故事性的琐碎情节和拖沓节奏中,假一二小物件如尺八、铜镜,小事项如秦腔、目连戏,串联起有时连自己都不能确知的民俗,然后再生造出几个一出场就自带光环的非聋即哑的奇人异士,乃或土匪、风水师,展开一个神出鬼没的奇特故事。更主要的是,总是以一种虚无的态度,渲染人在既有价值崩坍后找不到出路的绝望与苦闷,从而使作品呈现出沉迷、逃避的灰暗基调。
应该说,今天的读者已不会要求作家一定如先知,走在生活的前面,独自担荷着寂寞,给人类以希望;或掩身人后,成为传统悲壮的殉道。相反,特别能理解从那个年代走来的作家,虽物质上逃离了乡村,精神上常存在的与城市互不接纳的尴尬与紧张,并对由这紧张造成的精神危机,有感同身受的体谅。但这不等于说,他们会无原则地包容一种失去与社会相关性的创作,会对作家仅听命于个人臆想中的观念,既不体现人性的宽度,又缺乏生活亮度和生命温度的表达照单全收。事实是,从《古炉》《老生》到《山本》,甚至再往前推《废都》和《白夜》,许多时候,作者一直是在靠老熟的技巧和语言,重复着自己那些随生活状态固化而日渐颓唐的人生体悟,不过时常间杂一些道释思想与民间信仰,以增其神秘添其深刻而已。这造成他笔下的人物常常神神叨叨,他描写的乡村常常主观象征大于切实指呈。由于好用民俗的猎奇取代文化寻根,尤缺少对这种民俗背后的隐喻义作深刻反思与质疑,他对乡村伦序崩坍的哀叹,连同刻意的“自然史”的抒写方式,并未能开显出长久以来存活于中国民间的基础人性,更谈不到颠覆了过去刻板的传统叙事。相反,由于其写作的精神资源许多时候与当下的商州、西京和秦岭是脱开的,他对乡村的迷恋因此常常显得不很真实,而仅表现为一种不易为人认同的骸骨迷恋。与之相对应,他对城市的厌弃与反思,也就因此与一种反智与反文明的原始情绪眉目相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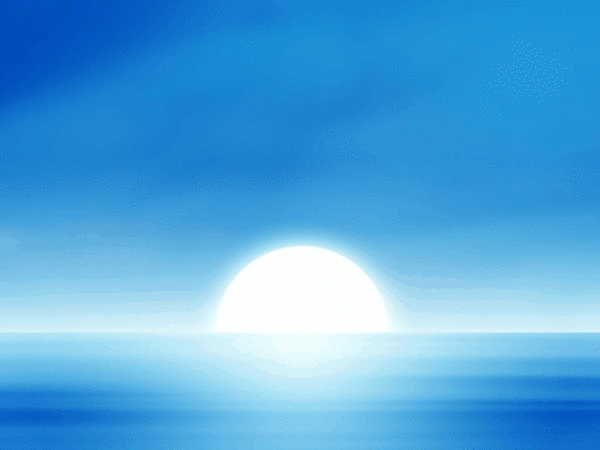
作者每出一书都偌大的阵仗,结果却像有的展览,开幕就是闭幕,这难道不值得我们的评论家与他一起深切反思吗
我们注意到,作者每出一书都会谈个人的困惑与痛苦,这自然赋予他写作的正当性。想问的是,人生在世,谁没有困惑和痛苦,生存的本质甚至不就可以说是痛苦吗?唯其如此,赫尔岑才说“一部俄罗斯文学史就是作家的苦役史”。只是好的作家不会因为痛苦,就用精神的颓废或肉欲的狂欢来逃避。相反,他们能体认到作为一种“堕落的存在”,人虽难弃俗世肉身,尤脱不开欲望的缠缚,但人生绝不是没有意义的尘埃。如果没有高上的道德视镜和敢于独立消解人生累累重负的勇毅与担当,只一味取消是非,漠视差别,视与世推移的看破为超脱,抽身事外的不介入为高明,甚至以虚无的出世描写来表达对人生广大的悲悯,而另一方面在艺术上又不能深自沉潜,仅以市井故事勉强敷衍,以去人物化的说理求得作品寓言性与超越性的实现,而忘了从故事到文学之间还必须经诗化的转换与提炼,这样的创作缺长久的感染力几乎是必然的。
但遗憾的是,很少有批评家指出这一点——指出作家当然可以并应该揭开陈旧的历史,但他的历史观却不可以是陈旧的,进而指出如以沾带着这个时代所有的鄙俗与乡愿为文学代言,绝不可能诞育可与苦难相对抗的真文学。从这个意义上说,阅世深久如作者,是不必总将“我的写作充满了矛盾和痛苦,我不知道该赞颂现实还是诅咒现实”这样的话挂在嘴上的。文学从没要求作家一定要做出这样的选择,并一定要在作品中直白地裸示出自己的立场。有时,真无须纠结于姿态的选择,你只要凭良知揭出生活的真相,就足够对得起文学。

准此,我们觉得不用对比婚姻不幸又双目失明的博尔赫斯,他为什么在直言所有的文学都在讲人生多苦的同时,仍认定它给自己带来幸福,使自己的心变得柔软,并有以心安;仅对照同时代的路遥就足够有说服力。路遥的一生充满着想出名、要翻身的欲望,这与他对文学的热爱交缠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你可以说他并不纯粹。但当真的投身创作,他是全身心的,紧贴着现世的土地,只有真诚,毫不做作,既不信命,更不服输。他的《平凡的世界》,从结构到语言多少有些粗糙,但那种无所避却的投入和热忱,至今仍给每一个奋斗中的平凡人以真切的感动。所以虽来不及开研讨会,书却一印再印,俨然成为经典。相比之下,作者每出一书都偌大的阵仗,结果却像有的展览,开幕就是闭幕,这难道不值得我们的评论家与他一起深切反思吗?
这样的反思,对作者和评论家来说固然有些尴尬,但却非常必须。
评论家需要在阅读与思考中安静等待。因为时间的沉淀与汰洗,足以使自己回归常识,并令一些玄虚的表达破功

由此我们想说,时至今日,已无须再在应重建专业而有诚意的批评上多费口舌,关键是如何建立。为此,必须确立一些“规矩”。
首先,必须熟读文本。这个道理人人都认。但落实到作者,有时以半文不白的语言,写不知身在何处的虚幻人生,满纸暮气,格调低迷,人物尤其怪怪奇奇,以至对人生苦难的体验,最后被转换成了对一种神秘力量的盲从。只要认真读原作,即使整体肯定,仍不会不觉得这是需要指出的瑕疵。不然,小说只能局限于个人化的抒写,不可能成为一个时代忠实的代言。但现状是,有多少批评是在这个起码的基础上做出的?对此评论家心知肚明,那些主动或被动赶场的一线评论家尤其心知肚明。
其次,必须引入更多圈外的批评。许多人都指出过,1980年代文学批评之所以活跃,是与大量“非学院”的批评家存在有关的。这里,我们要进一步指出,那些非当代文学专业批评者的声音,有时更值得倾听。譬如有评论家并无详细论证就断言《山本》是继《老生》后,进一步推进对中国近现代史的理解与思考的成功之作,又称作者固然是为秦岭写志,其实是为近代中国写志。这样的判断如能出自治近现代中国史的专门家之口,或者有这样的专门家的加持,会更有说服力。而我们也没理由怀疑,这样的专家就一定没有判别自己母语文学的能力。今天的评论界,评论家与作家之间似已形成了某种固定的“对位”关系,如重量级对重量级,这使得有的评论家似比作家本人更急切地期待并乐于在这种时候应景出场,这实在是很要不得的事情。

最后,必须要有沉淀。当一部新作问世,评论家需要在阅读与思考中安静等待。因为时间的沉淀与汰洗,足以使自己回归常识,并令类似“《山本》打开了一扇天窗,神鬼要进来,灵魂要出去”这样玄虚的表达破功。足以让自己在尊重作家为人贡献了独到的经验同时,更想揭出好的文学必定是努力介入社会,并经由拷问人物进而审视自己的那种。如果它进一步还能与读者一起,将人与一种将要到来的意义联系在一起,就更好了。在这方面,时间曾经并必将继续发挥它无可代替的作用。而经由时间的沉淀,脱去了浮躁与误判,甚至一定程度免除了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把友谊放在真理之前”的窘境,批评必能使自己成为如夏普兰所说的“一种向作家提出有益告诫的艺术”,而批评家也真有可能就此重掌“经典确立者”的权杖。这有多好!

(作者系复旦大学教授、上海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作者:汪涌豪
(图片另附)








发表评论 评论 (3 个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