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嘉宾:
胡 香 张 翼 宁颖芳 荣润生
罗 凌 鲍伟亮 高 超 熊 轲
应该说,宿命般地与写作(不限于文学,可以是所有的艺术表达)结缘,是发生在少数人身上的事情。而且,这其中也不排除某些偶然性因素的存在。天赋异禀于他们而言,与其说是上天的眷顾,不如说是一种磨难,甚或灾难。然而,这样的命运背负在他们诗性的心灵或人格当中,进而会发展为一种使命,以自己的血肉之躯点燃并作为献祭的艺术使命。
写作受命运所使,写作本身也足以构成一种命运。就像诗人宗霆锋在评论胡香时说的:“深入真正写作时必然要具有的涉及精神之黑暗的勇气……诗歌对诗人的驱策何等残酷!”那是包括诗人在现实命运之外的一种“灵魂遭际”。而这“灵魂遭际”,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并构成诗人的现实命运。
当写作出离天真、自负的阶段,出离某种极端的孤独与神秘体验,以及少数天才个人的特异境况,或许就会呈现一种明白、明朗的“日常”面孔——写作源于热爱,是主动选择的结果。或者说,是来自于人和文学(艺术)的双向选择。
设置这样的话题,是想看到不同观念,甚至完全针锋相对的观点的碰撞。或许,还有其他可能性。毕竟,对于我们的生命,精神世界的幽暗莫测,生存现场的灼热惨烈,以及写作本身的无法穷尽,均非寥寥数语所能阐明。
——主持人语(王可田)
写作是命运所使吗?
胡香
我想,并非所有写作都与命运有关。写作(以及别的表达方式)与命运发生关系,应当从彼此凝视开始。
尼采说的“当你凝视深渊,深渊也凝视你”这句话里的“深渊”是可以用来置换的词,比如“命运”,比如“灵魂”,比如“神”……这些难以指认、无以为证的存在。
关于命运,关于写作,我都所知甚少。在我看来,写作以及阅读的最大意义,也许就在于问询命运,个人的,人类的,以及写作者所能触及的一切事物的。
荷尔德林说:“我在说天书,但是它存在。”当你深深感知某种强大无比的,对人,对人类,以及万千事物,不为人知的影响力,它时时刻刻地存在着,却难以把握,无法指认(化学的?物理的?数学的?生物的?……都是,都不是。迄今为止,人类所有知识的终端都只是通往神秘未知的途径)时,彼此的打量与凝视开始了,你已抽身不得。“命运”不过是人们对这种未可尽知的影响力的权且命名之一罢了。
人,是经不住这种凝视的。在长久的凝视中,产生探寻,产生纠缠,产生对峙,产生冲突,产生抗争,产生融合乃至顺服……而首先被摧毁或吞噬的,往往是人的意志,而非命运或神的意志。因为后者未知的力量,远远,远远,远远大于人,乃至人类所能调动的已知力量的总和。人,是被自身的局限和越境的迷途击溃的。
海子说“我走到了人类的尽头”。沿着尘世繁华的道路,瞬间走到人类尽头的,岂止海子呢?
在问询命运的道路上,我永远敬仰和追随的,是那些“来吾道夫先路”前赴后继的探索者与牺牲者,而非别的(比如成功学和算命先生所指引的个人前程之类)。

胡香 1964年9月生, 作品发表于《诗刊》《美文》《延河》《小说评论》《文学家》《文学报》《延安文学》等报刊, 出版诗集《摇不响手上的小铜铃》。
张翼
宇宙是如何产生的?是如何结构和运行的?为什么会产生生命和智慧?宇宙和生命是无目的而又合目的的吗?或者,宇宙本身就是具有人格意义上的智慧体,就像我们的大脑?对于埋头过日子而言,问这些问题有意义吗?宇宙、太阳和地球不就是用来过日子的工具,一如我们的汽车或铁锹吗?
然而,对于那些喜欢仰望星空,和那些带着特殊才能,或许还有“一定要……”的决心,来到这个星球上的人,他们的所作所为只是个人权力意志的体现吗?还是被宇宙或其创造者赋予了某种使命?我这样说是在故弄玄虚吗?人不就是一架有机分子机器吗?思想意识不就是这架机器的机能吗?那么,人不是只应该听命于这架机器的需要,听命于欲望吗?为什么他反倒要按照头脑中虚幻的概念去行动呢?人不应该是概念的主人吗?为什么会沦为概念的执行工具呢?
所有这些问题,我思考,却没有答案。但有一点我体验得非常清楚,那就是我的感受、情感和思想并不都是来自于自我内部,有很多是来自于宇宙天体的性质不同的能量,我们需要也能够去辨别它。写作是否是一种宿命?对我来说,这个问题只是一连串更大更普遍更基本问题的最末一环。

张翼 1971年生,陕西宝鸡人。陕西省作协会员,陕西省诗词学会会员,陕西省青年文学协会会员,柞水县作协秘书长。曾任外科医生,后弃医从文。著有《漂流瓶里的诗篇》《存在论》《梦境》等。
宁颖芳
某种意义上,写作似乎是命运的安排。一个内向敏感而又爱幻想的乡村女孩,在贫瘠的童年和孤僻的少年时代,最喜欢在课外书籍的阅读中感受外面世界的美好。我迷恋文字带来的种种丰富的情感况味,以及对心灵世界潜移默化的熏陶与抚慰。小时候写的作文一直被老师当作范文在课堂朗读,它带给我的自信快乐以及小小的虚荣心和满足感,让我喜欢上了写作。我开始在日记中写下我的梦想、欢笑与泪水。一直渴望逃离乡村去远方,渴望逃离现实去一个虚幻美丽而又迷人的世界,而写作就是飞翔时生出的羽翼,是从此岸到彼岸的舟楫。那些曾在日记中写下的分行文字,当时只是一种心情的记录,后来渐渐成为梦想最初的画面。从十八岁上大学中文系至今,写作一直断断续续地陪伴着自己。
感谢生命里有文字一路相伴。一张白纸有博大的胸襟和悲悯的情怀,让我们在世俗琐碎的生活之外,能够感受到精神世界的丰富多彩。在白纸上写下黑字,仿佛在描摹命运的图案,在与知己交谈,和朋友诉说。文字所构筑的世界是绚丽的,温暖的,它给予我继续走向明天旅途的勇气和力量。
写作是命运所使,是我与自己心灵对话的一种方式,是人生迷雾中的一盏灯,是开启命运之门的一把钥匙。

宁颖芳 1971年,中国作协会员、陕西省作协理事、咸阳市作协副主席、《秦都》杂志主编。著有诗集4部,散文集3部。
荣润生
如果卡夫卡的父亲性情温和,卡夫卡又不敏感、怯懦,他就写不出《变形记》,格里高尔也不会变成甲虫。卡夫卡在《致父亲》中说:我写的书都与您有关,我在书里无非是倾诉了我当着您的面无法倾诉的话。
命运安排博尔赫斯出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书香门第之家,一出生嘴里就含着一把开启图书馆的金钥匙。7岁用英文缩写了希腊神话,后来遍游英法。三十岁又受命运驱使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图书馆并终身从事图书馆工作。一生成就显赫,被称为作家中的作家。
我明明知道写诗不仅不能致富,反而会倒贴时间、精力、钱财,却不管不顾一根筋写了四十多年,至今一事无成,仍然执迷不悟。早在三十多年前就有文坛大佬告诫,如果写作几年仍不能够成名,趁早改行。事实证明他所言极是。但这么多年我仍然不忘初心,贫贱不移。这种愚痴究竟来自哪里?不能不说是身不由己,命里安排。
可以失败,不可以放弃。聂鲁达说:“对我来说,写作就像呼吸一样,不呼吸我就活不成……”爱好者亦如是,靠写作活着,以写作延续生命。还有许多人正等着我把他们写出来,等着我的笔尖点活他们的眼睛,等待我的诗歌赋予他们三魂七魄。也有许多文字正等着我把它们组合成情感、美和思想。

荣润生 笔名,雨生,太原人,现居江苏昆山。山西省作协会员。著有诗集《我的心烫着了黑夜》(长江文艺2017年出版)。
罗凌
写作是命运所使吗?这个问题应该分三个层面来解读吧。怀有大才华的天才作家,写作就是他的命运;当下是全民写作的时代,对普罗大众来说,写作是情绪的出口,观点的表达,自我消遣的方式,或者就是为了挣流量赚钱;还有一部分把写作当成事业的人,写作对这些人,应该是承担现实苦难,面对心灵责任,把知识化为文字的一种劳作。不写不行,必须写——这并非命运驱使,而是或大或小的担当精神。
尽管每个人写作的原因不同,但内心深处的童年,对现实的关照,所处的地域,经历过的人和事,都会关乎写作的高度和格局。相比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繁盛的时期,现在的文学越来越边缘化、圈子化了。“文学永恒的魅力,在于探索人类精神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我始终坚信,只要有人在地球上栖息,文学就不会消失,写作这种特殊的劳作永远存在。
每个写作者都会面临一个问题:写作进入到一个层面,会出现难以突破的瓶颈。这时候需要停下来,阅读、行路,干点别的事,再提笔尝试另一种体裁和表达方式力求突破,别去想是不是命运所使,调整心态,克服焦虑是最重要的。
对文学越是热爱,越会觉得它不是单纯的爱好,而是一种信仰。作为一个写作者,无论它是不是你的命运,都应该把文字当作图腾,以一种敬畏之心去对待。这样,才可能走得更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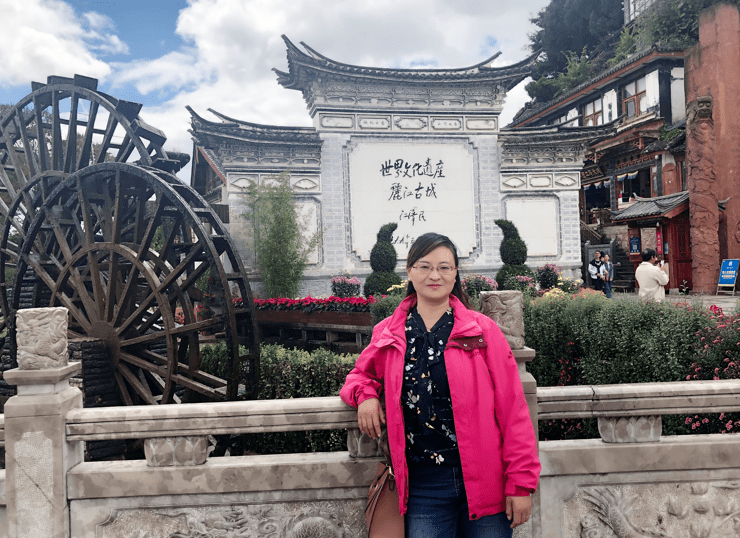
罗凌 藏族,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四川省作协会员。有多篇文章发表于《西藏文学》《青年作家》《美文》《民族》《四川日报》等报刊及网络平台。
鲍伟亮
写作受命运所使,但命运却并非影响写作的全部。
命运代表着什么?生命航线的轨迹,因为未知和某些不可更改性,使其神秘而冷酷。当生命的轨迹随着时间的迁移不断展开,便展现出生活的跌宕与玄奇,而生活,正是写作的源动力。
写作离不开外力的刺激,当现实中的境遇对人造成影响,内心产生了表达或者发泄的诉求,其中的一部分人便以写作的形式将这些感受表达出来,并随着生活后续的发展,将这种抒发形式继续进展下去,当然,抒发的冲动也有可能逐渐被磨灭。不论写作的后续如何发展,却注定了写作与生活之间的必然联系。
生活是经历者描述经历所创造的词汇,命运是经历者描述所有不可预知以及无法更改的经历所创造的词汇,故而,命运应当属于生活的某个重要部分,即神秘与不可测的概述。
总而言之,写作,必然在命运的影子之下,与其直接相关的却是生活对人类的反馈,无形的感受以有形的方式表现出来。

鲍伟亮 1997年生,山东莱阳人。作品散见《诗歌月刊》《星星》《山东文学》《诗潮》等刊物及多个选本。
高超
关于写作是不是命运所使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要考虑一个作者是因何而写作的。
有的作者把写作几乎看作是自己生命的全部意义,在写作上充满了雄心壮志,认为写作足以比拟生命,就像马尔克斯那样,如果不能写作,那么宁愿死去。有的作者则把写作当成一种兴趣爱好,在写作上没有大的野心,只是想通过写作来让自己获得精神层面的满足。然而无论前者还是后者,他们选择写作,一定都是因为内心有着表达的欲望。说到表达欲的产生,这里又分为了两种情况。一种是作者有着丰富多彩的生活经历,对世态炎凉有了非常深刻的认识,积攒在内心深处的一些人生感悟需要通过某种途径表达出来,最终发现写作是适合自己表达内心的途径,因此就把写作当成了自己生活中的一部分。另一种情况是因为自身对文学产生了热爱,感受到了文学的召唤,因此成了文学的信徒,开启了属于自己的写作之路,就像陈忠实先生因在初中时读到了赵树理的短篇小说《田寡妇看瓜》,于是便对文学产生了热爱,数十年间笔耕不辍,终成一代名家。
说到这里,就很容易回答“写作是不是命运所使”这个问题了。要知道,很多人虽然有着丰富的生活经历,但并没有选择通过写作来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而有些人的生活经历非常苍白、单调,上天并没有给予他太多的所谓的创作财富,但却能成为文学界的佼佼者。
因此说,写作并非命运所使,写与不写完全取决于个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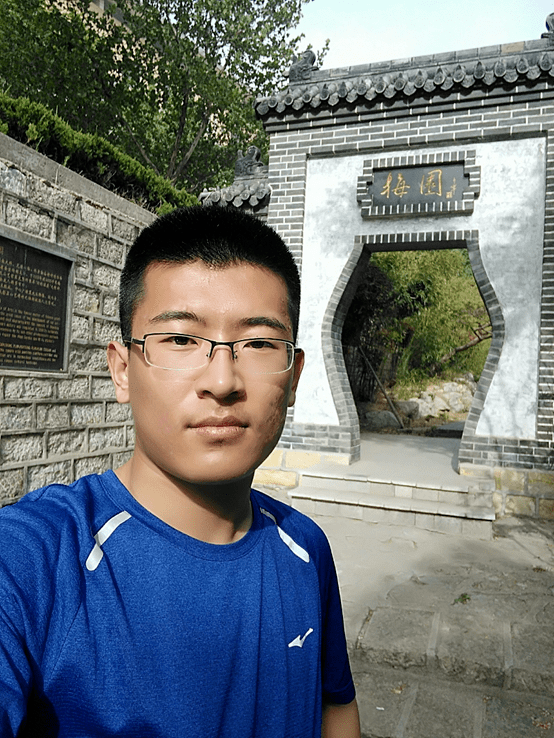
高超 1998年生,山东安丘人。现为山东艺术学院2017级戏剧影视文学专业在校生,有散文刊于《人民文学》(增刊)《北京文学》《散文诗》《岁月》等,书评刊于《亮报》《湘声报》《京郊日报》《牛城晚报》《曲靖日报》等,曾获第七届“观音山杯·美丽中国”海内外游记征文佳作奖。
熊轲
写作是命运的所使。小时候拥有许多梦想,随着年龄的增长都揉进了岁月里。那时候的我常常因为背书备受责罚,口中也就留下了讨厌文字的判断,可不知何时渐渐偏爱起语文,总想在书中一尝饕餮盛宴的滋味。于是发现文学这东西不是职业,亦非爱好。而是在某个瞬间获得的一份命运的使然。
时光总是驱赶生活向前,我们无时不在规划自己的未来。人傻傻地在理性中奔波,这是自己肉体屈服于潮流的暗示吧。然我们并不反驳一件被确切证实的事情,即人是会做梦的。所以我可以判断人是浪漫的。浪漫作为人独有的“激素”,在命运中鼓励人主动探求能够代表自己特有价值的个人哲学,于是发现文字成了命运的载体,写作也就成了抽象的具体表现。渐渐地内心也就多了一份不曾探索,却自然而然产生的渴望,至于这种命运所使是否被个体所把握,那便是个体与个体之间差异性所决定的。关于我,那一番对写作最初始的悸动,确实是被命运所促使的吧。
大抵俗世倾泄千百种劫难,为某个有限的命运个体带来无限桎梏,文字为开拓命运宽度的契机,把握住方能成就本我,故而终能思维之滥觞。相对于碌碌无为的大多数,不枉在一瞬风骚之中洞察万籁。由一种被动逐渐转化为主动,一个文学创作者是必然经历的。偶尔深陷囹圄,亦可清歌。写作扎根命运,不枉走一遭人世。

熊轲 吉林动画学院在校大学生。河南诗词学会会员、河南省青少年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于《中华诗词》、《长白山诗词》《文学少年》《中华儿女》(海外版)等。
来源:绿色文学(微信公众号)|选自《延河》下半月刊2020年8期








发表评论 评论 (1 个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