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31日,三联学术论坛第11期,“林中响箭——杂文的自觉与鲁迅文学的‘第二次诞生’” 在北京三联韬奋书店·美术馆店二层举行。纽约大学比较文学系教授张旭东,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孙歌,作家余华,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李敬泽参与讨论并发言。论坛由美国布兰迪斯大学外国文学系副教授、比较文学项目主任王璞担任主持人。

美国布兰迪斯大学外国文学系副教授、比较文学项目主任王璞
今年7月,学者张旭东的新书《杂文的自觉——鲁迅文学的“第二次诞生”(1924—1927)》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推出。书中,作者提出鲁迅杂文虽然诞生于新文学的第一个十年,但它同一般的现代白话散文的关系,却如同量子力学同牛顿力学之间的关系。“就是说,在文学意识、作者意识、形式强度和风格总体性等方面,它与同时代的写作之间保持着一种代差或‘降维打击’能力,并把这种结构距离一直保持到20世纪的终端。”

《杂文的自觉——鲁迅文学的“第二次诞生”(1924—1927)》 张旭东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3年7月
张旭东认为,这种结构性代差不仅具有形式和审美内部的价值和意义,也在鲁迅杂文的现实表现和历史表象领域打开了一个新的空间,这就是鲁迅晚期杂文在编年体合集意义上形成的“诗史”气象。“杂文的自觉”是鲁迅杂文本体论或存在论意义上的整体自觉,它同时开启了鲁迅文学形式空间和历史空间的自我建构。
7月31日的论坛上,王璞在开场白中介绍说,今天活动的副标题就来自张旭东的新书。“就像张老师在书中的前言所说的,在我们每个中国人的头脑里,鲁迅的作品总有其影子,总是运行在我们意识的后台。就好像大家拿着手机,其实它总是那个后台运行的程序。他总游走于我们视野的边缘,他足够熟悉,无须提起,但又是一个未解决的问题,更切近于当下。”
而针对此次论坛主标题“林中响箭”,王璞在现场朗诵它的出典 :“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一切所谓圆熟简练,静穆幽远之作,都无须来作比方,因为这诗属于别一世界。”(鲁迅,《白莽作序》)
《杂文的自觉》作为张旭东细读鲁迅“三部曲”的首部专著,全书立意对于世人眼中既是文学家,又是思想家、政治家的鲁迅的形象予以廓清,认为鲁迅的文学才是第一位的,只有在鲁迅的文学性中读者才可能走近鲁迅的思想和政治;其次,杂文在鲁迅文学分析中的首要性,也就是说鲁迅的文学性其实是杂文,而不见得是小说、散文诗;最后,鲁迅的现代主义特征,主要也体现在杂文上。

纽约大学比较文学系教授张旭东
杂文,是鲁迅在意识层面和无意识层面的唯一选项
活动当晚,受台风“杜苏芮”影响,北京全市强降雨来袭,三联韬奋书店论坛现场却座无虚席,张旭东在发言时首先向全场来宾表示了感谢。
他认为鲁迅作为新文学的第一代作家、起源性的作家、前卫作家和奠基性的作家、标杆性的作家,他必然要承担一种文学使命。“无论在意识层面还是在无意识层面,鲁迅都有自己的考虑。无意识层面可能就是表现为焦虑。鲁迅考虑更多的问题是怎么写的问题,而不是写什么的问题。写什么的问题相对来说外界条件帮鲁迅解决了,有人来骂他,他就知道该怎么写了。碰到军阀、碰到裹小脚的,碰到一夫多妻制的,他就知道写什么了。外界不断地告诉鲁迅要怎么写,最后他意识到这是他没得选择的一种选择,这种外界的强加几乎到了令他窒息的地步,所以鲁迅的写作在生理意义上是一种反抗窒息的呼吸动作。”
“而在意识层面,新文学第一代作家都会考虑到一个问题:白话文不只是白话,不是从文言里摆脱出来,吾手写吾口这就够了。白话还要有‘文’,还必须在‘文’的世界里站得住,要有艺术的标准,要有风格,要有形式,要有修辞等等。鲁迅曾自道他存在的状态始终是处在歧路和穷途,没有路要走出一条路来。做一个一般意义上的小说家或者诗人,解决不了他内心最核心的心病。”
“在这点上,鲁迅给自己作为一个作家过早地施加了太大的压力。任何人侵犯他关于他写作的底线时,他认为这就是对他存在本身的冒犯和侵害,所以他是以一种政治性的敌我之争,生死搏斗的这态度去应对的。可以说他是把文学写作内部的艺术问题、审美问题充分政治化,然而在表达方式上又是一种诗的方式或者说文学的方式,我认为这是鲁迅文学一个基本存在的样式。在这样的情形下,他最后找到杂文作为自己唯一的选项。”张旭东说。
鲁迅所有的文字里,都包含了杂文的灵魂
孙歌在发言时,以鲁迅的《夏三虫》《从帮忙到扯淡》《我要骗人》三篇杂文为例,认为这些杂文中都展现了鲁迅对于讽刺的自觉。“他说讽刺当然没有幽默那么优雅,它有点危险,但是讽刺一定是以真实为生命。当一个人可以用精炼的和艺术的笔调勾画出某一群人、某一些真实侧面的时候,这就是讽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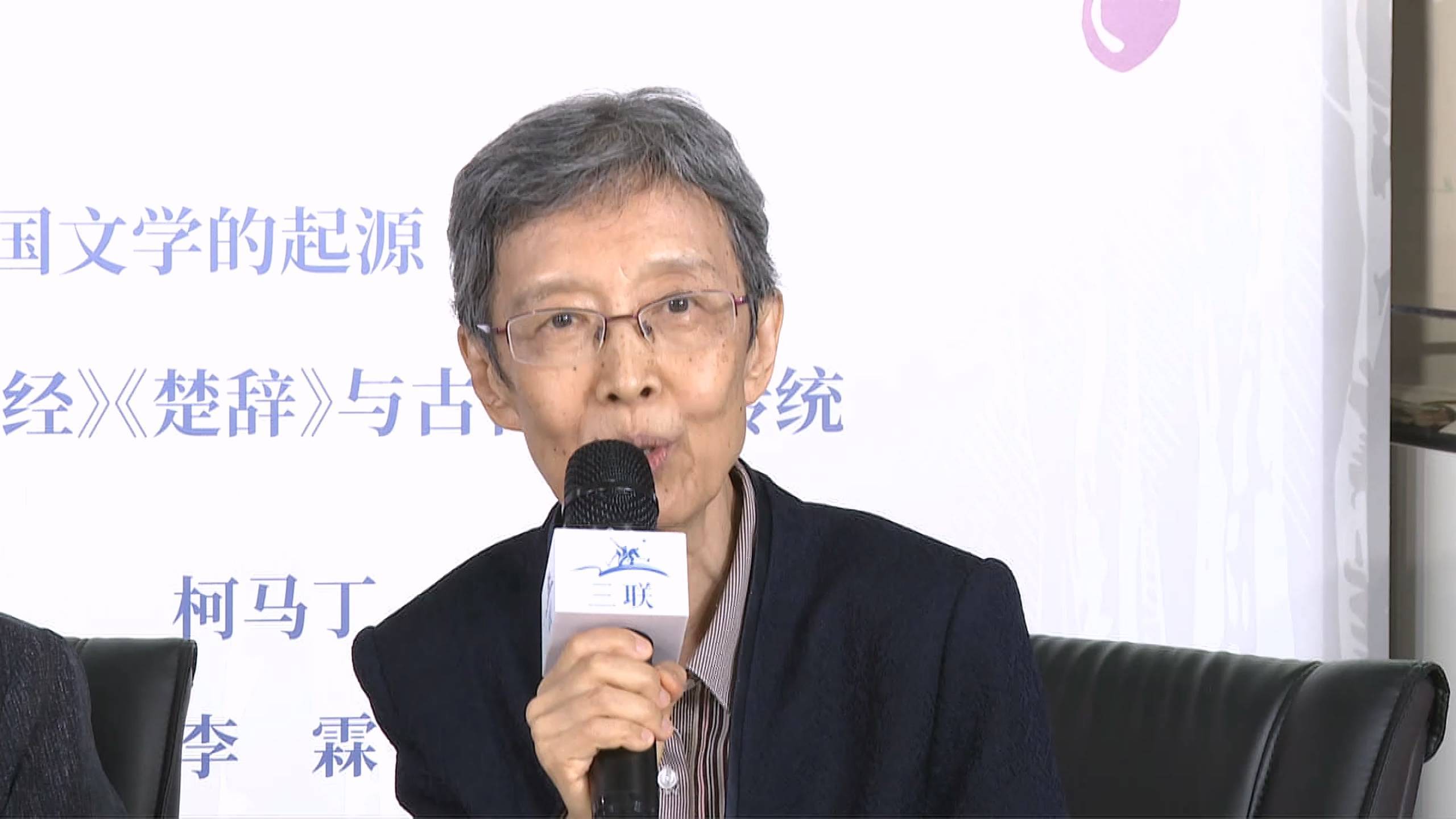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孙歌
孙歌认为《杂文的自觉》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具有颠覆性的视角,“在鲁迅所有的文字里包括小说诗歌散文,以及翻译和学术史研究中,所有的这些文字里都包含了杂文的灵魂,所有的这些文体都可以看成是鲁迅杂文的一种特殊形态。这为我们大家打开了一扇窗:从鲁迅杂文的世界,进入鲁迅全部的文学世界。”
“同时这本书里包含了两个主题:显在的主题叫做‘杂文的自觉’,主语是鲁迅,这本书就是以鲁迅写杂文的心路历程为结构来串联的;另一个浅在的主题,其实在这本书里占据的篇幅一点都不少,就是‘自觉的杂文’,主语是杂文,也就是说当张旭东处理鲁迅‘自觉的杂文’时,他必须要进行大量的、非常细致的文本分析。”
“比如在书中有段话,这段话我等了很多年,终于有人把它说出来了。鲁迅当年在他的那些论战里骂错了很多人,而且有些学者用学术的方式证明鲁迅把谁给骂错了。但是骂错了人的鲁迅为什么还是鲁迅?我们为什么还是喜欢鲁迅的杂文包括他骂人的杂文?当然鲁迅自己在讲讽刺的时候已经间接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不必是曾有的实事,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
“我觉得旭东这几句话非常精炼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在鲁迅的种种题记里,执滞于‘小事情’是最令人生畏的,可以说它是鲁迅杂文风格的实质所在,这种实质不止关系到杂文的内容,也决定了杂文的审美构造。执滞于‘小事情’把人的意识从种种冠冕堂皇的大事情上转移开,从种种以历史文化、道德不朽等名目的虚伪和颓废中转移开,将它聚焦凝固在当下和此刻突如其来的瞬间,使杂文和新文学语言在无可回避的具体性个人利害关系和情绪投入中,远离了种种制式化、形式化的陷阱。这点写得非常精彩。”孙歌说。
鲁迅血管里喷出来的就是杂文
余华在发言时表示,自己在年轻时很讨厌鲁迅。“大概到了我35岁的时候,有一个机会重读鲁迅,那个时候才真正开始读鲁迅。后来我开始发现这种现象也不是中国特有的,全世界都有,挪威的学者作家小时候也讨厌易卜生,印度的作家小时候也讨厌泰戈尔。全世界当你的阅读是被强压下来的时候,一定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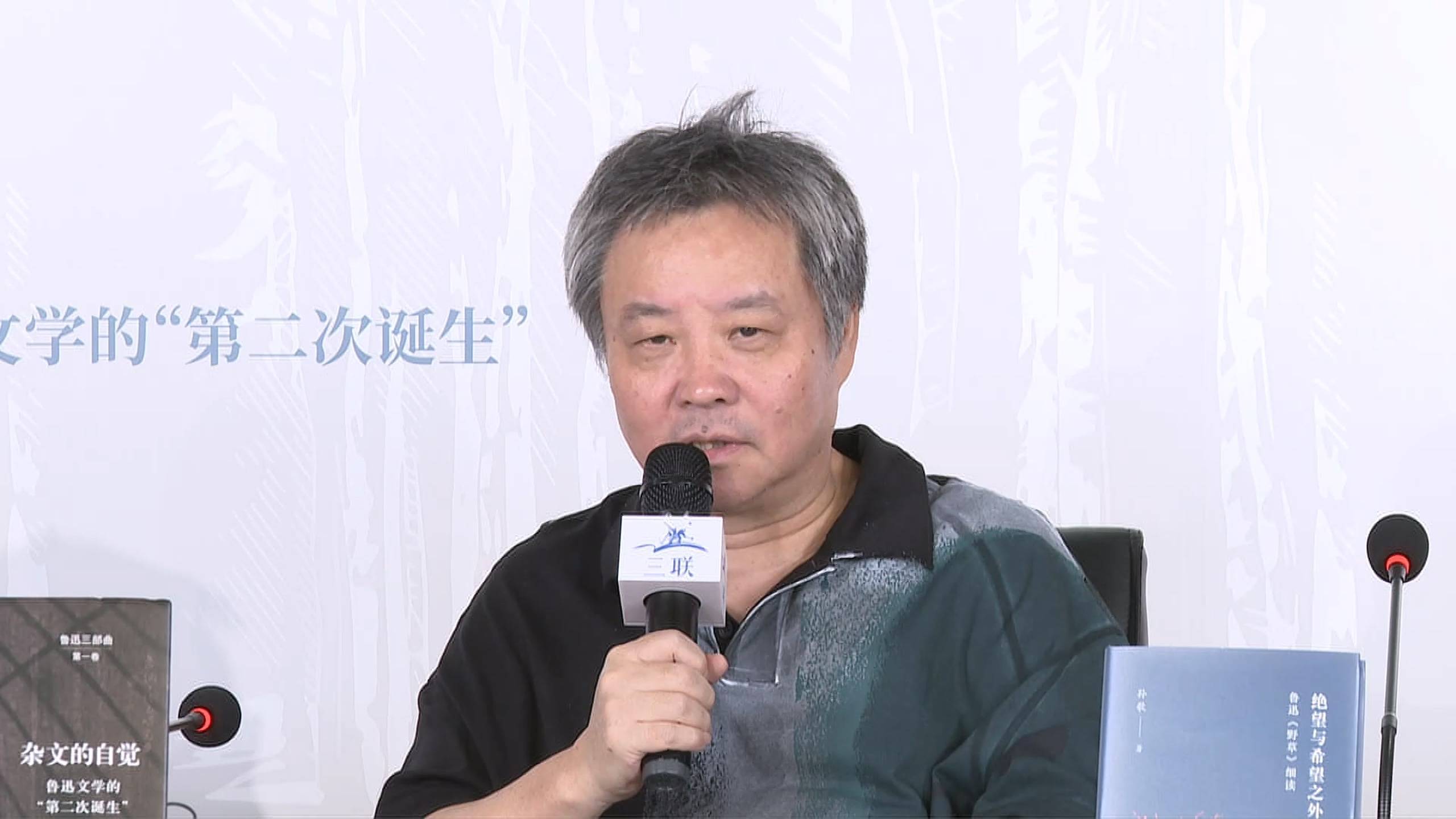
作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余华
余华自道,自己对鲁迅的小说要比他的杂文更熟悉,但是很奇怪,记忆里一些好玩的东西往往出现在鲁迅的杂文中。“鲁迅和小说的关系,以及鲁迅和杂文的关系,前者是鲁迅要去写小说,后者则是杂文要鲁迅去写。鲁迅的杂文从《热风》开始,一直到《坟》,文体很散漫,长长短短都有,到了《华盖集》才感觉到结构稍微严谨一点。这让我感到,鲁迅要是没有那些‘蚊子’和‘苍蝇’的敌人,他真写不了那些杂文。”
“鲁迅文学里最根本的是什么,是人的根本。过去,我们称鲁迅是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政治家、教育家,好多‘家’,但鲁迅根本上是一个文学家,因为只有文学家才能够把最根本的那些东西写出来。在世界作家里仔细想一想,能够跟鲁迅比较接近的是博尔赫斯。但他们两个人截然不同,博尔赫斯永远不写根本的东西,我们年轻的时候往往会崇拜博尔赫斯,因为他的笔下展现了人的智慧。但鲁迅从来不说聪明的话,他写的都是人最根本的问题,而且这些根本的问题都是小事。”
“鲁迅去世快90年了,如果从他的成名作,1918年发表在《新青年》上的《狂人日记》上算起,一百年都过去了,我们还在读鲁迅。”在余华看来,鲁迅既不崇洋媚外,也不厚古薄今。“他专门有一篇杂文叫做《人心很古》,从这点看得出,他血管里喷出来的就是杂文。”
鲁迅作为文学的杂文,或为当下的时代所鉴
李敬泽在发言时介绍说,自己现在仍在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张旭东的《杂文的自觉》一书中很多文章最早是在《丛刊》上发表的。

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李敬泽
“张旭东在这本书中提出鲁迅文学的第二次诞生,这是非常重要的命题。因为在鲁迅作品的传播中,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我们接受的主要是他的小说、散文诗,对于鲁迅杂文的文学性还没有一个系统的认识。学界到现在还在探讨鲁迅为什么没有把更多的精力花在写小说上,言外之意对于他写杂文的意义是有质疑的。张旭东这本书有力地回击了这种质疑,提出对于鲁迅而言,写杂文就是进行文学创作,而且他认为把杂文作为文学创作也是鲁迅的首创。鲁迅的杂文有一定的审美构造,是在作家的思维存在论意义上进行了深刻的概括。”
“过去我们理解鲁迅的杂文,是在文类学区分意义上的杂文,张旭东在书中提出了杂文的自觉,实际上是认为杂文不仅仅是一个文类,而是一个从世界观到方法论,再到修辞、遣词造句这样一套系统的文学精神建构,它具有文学构造和审美构造。同时,这样的阐释不仅仅是让我们重新理解、重新认识鲁迅,也要思考鲁迅在杂文中的自觉,为什么没有在后来的现当代文学发展中,被自觉有效地传承下来?这其实是很大的问题。鲁迅在存在论意义上、在审美构造意义上的认识,其实并未得到当下人充分的认识和领会。”
李敬泽认为,鲁迅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永远向我们提出问题,我们也永远从他那里得到启发。“之前我们只把鲁迅的杂文当做杂文,当成他骂人的文章,这是我们没有读好。我在读《杂文的自觉》时一直带着问题意识,在当下这样一个文化生态下,考虑到我们每个人的生存状态,书中所阐述的鲁迅的杂文精神,鲁迅的作为文学的杂文,很可能,也应该为当下的文学开辟出新的空间、新的可能性。我真是觉得在这样一个互联网传播的条件下,在这样一种混杂的传播条件下,当初鲁迅从一种文学角度来构造出的杂文,也许他就是为我们这个时代构下的。”









发表评论 评论 (6 个评论)